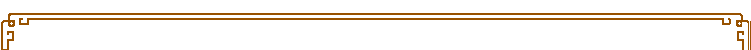回到莫斯科以后,我看见我们的歼击机还停在车间里。
12月底,斯大林打来电话想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并问我能否履行诺言——1月1日前拿出飞机。
我履行了自己对政府的诺言。歼击机“伊-26”(即“雅克—1”)在1940年1月1日前就已推到机场。
继它之后,“米格”和“拉格”飞机也在1940年春搞出来了。其他歼击机是在这年夏天搞出来的。
在政府选定的所有歼击机中,“拉格”、“米格”和我们的“雅克”工作进行得最为顺利。对米高扬、拉沃奇金和我都催得很紧,而且不管我们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给予我们帮助。为了加快凋试和试飞的进展,还与批生产厂打通了关系。
首先制成的“雅克-1”歼击机从我们设计局的装配车间被送到了全国最好而生产能力又强的一个工厂的机库。当时这个厂的厂长是帕维尔·安德烈耶维奇·沃罗宁,总工程师是彼得·瓦西里耶维奇·杰明捷夫。他们对试飞准备工作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
工厂全体人员的工作非常紧张,随着工作接近尾声,他们就更加紧张起来了。如果说当初要让某个人承担一项工作,或者要他留下来多工作一会儿和加一下班还要劝说的话,那么到快要制成时,人们便自动地不离开设计局和车间了。
最后,飞机停在机场上了。它匀称挺秀,伸展着双翼,好象自己准备飞起来似的。
我们好几百工作人员的心情都异常兴奋,因为每个人都看到飞机上有自己一份劳动。不过,每个人的心里也很担心:不知道这架飞机的表现将会怎样?会不会出问题?
在开始准备首次飞行时,紧张到了极点。在飞机出来之前的最后几个夜里,我几乎没有合过眼。当时感到,虽然一切都经过了计算和检查,但毕竟还可能发生某种意外,怕的是并非所有计算都一定是正确的。
首次飞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试飞仍由尤利安·皮昂特科夫斯基进行。
飞机从机库里推出来,甚至已经过了上千次检查。皮昂特科夫斯基坐进座舱,检查了发动机的工作情况。拿开了机轮前的轮挡(放置轮挡是为了在发动机试车时飞机不至于滑动)。飞机终于起动了。
通常按照试飞的惯例,飞行员先在地面滑跑一阵,以便检查刹车装置、机轮和舵面是否灵活好用。当认为一切都正常时,他便滑跑到机场尽头,把机头转过来,朝向逆风方向。
不知怎么搞的,工厂里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试飞的详细安排和钟点。我们的工人们和设计人员,有的突然来到了飞行场地,有的爬上了工厂的房顶。他们和我一样,都非常激动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初生子”迈出的头几步。
我与我的几个最亲密的助手站在机库旁边。说真的,我当时好象患了疟疾一样,浑身都在哆嗦。当螺旋桨转动起来使桨叶形成一个银白色的圆盘状时,飞机后面尘土飞扬。看来是因为飞行员开足了油门,飞机便滑跑起来,在地面与飞机之间逐渐拉开一道狭窄缝隙,而且这个缝隙每秒钟都在不断扩大。最后,当飞机大角度向上爬升的时候,在我们头顶上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这真棒!” 不知是谁大声嚷道。
大家都感到松了口气。可是,皮昂特科夫斯基很有信心地在机场上空又飞了第二圈。
眼下情况还不错。不过事情并没有完:还不知道降落时会不会出问题呢?
飞机逐渐下降,并进入着陆状态。这是新机生命攸关的时刻。飞行员很有把握地进行下滑之后,飞机便在机场中心接地了,经过短距离着陆滑跑就滑行到了机库跟前。
这时我们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大家不分官职高低和年龄大小,都直向飞机奔了过去,把飞行员从座舱里拖了出来,将他抬起来往上猛抛。
没等皮昂特科夫斯基说话,我就已经根据他脸上那满意的神情和笑眯眯的双眼知道一切都很顺利。
“米格”、“拉格”和“雅克”飞机几乎是在同时试飞的,前后相差不到两三个月。这三种飞机都于1940年5~6月投入了批生产。
伊尔型、彼型、米格型、拉格型和雅克型飞机的生产,不仅意味着苏联空军由于有了十分现代化的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而使它的面貌为之一新,而且对国家来说,更大的意义还在于造就了一批富有创造性的年轻设计力量。
从1939年夏天起,斯大林就开始召见我,以征询对航空问题的意见。
最初由于经常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秘密讨论重大问题,使我感到有些窘困不安,特别是当斯大林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要说的? 您是怎样想的?”
当他想了解我对这个或那个工作人员的看法时,往往使我感到不知所措。
他看到我有些为难和不好意思的时候,总是鼓励我说:“您怎么想就怎么说吧,别不好意思——我们信任您,尽管您还年轻。您是行家,和过去的错误没有联系,因此比起老专家们来,可能更客观一些。我们过去对老专家也非常相信,可是他们却把我们的航空事业引进了泥坑。”
就在这个时候他还对我说:“我们不知道该相信谁。”
1939年一个炎热的夏天,波斯克列贝舍夫来电话要我赶快去一趟。十五分钟之后,我就到了克里姆林宫。
波斯克列贝舍夫刚一见到我就说:“快去,大家都在等您”。
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正在办公室里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互相打了招呼之后,斯大林马上就问道:“我们正在和伏罗希洛夫争论,对于歼击机来说,到底什么更重要:是速度还是机动性?飞行员的看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机动性,有的则说是速度。所以我们决定问问设计师。请谈谈您的看法好吗?”
我回答说,西班牙的空战经验对这个问题已经给了很有说服力的答案。当德国人在那里还未使用快速“梅塞施米特”之前,我们的飞行员曾经驾驶机动灵活的“伊-15”和“伊—16”打败过敌人。可是随着“梅塞施米特”的出现。我们的飞行员就感到很困难了。
“您确信,强调高速歼击机我们不会犯错误?”
“我确信,斯大林同志,”我回答说。
“我也是这样想的,”斯大林说,“可是他(指伏罗希洛夫)却表示怀疑。”
“今天真闷热,”伏罗希洛夫敞开了元帅服上衣的领子,而且为了避免进一步争论下去,对斯大林微笑着,并向我点了点头说:“他倒不错,你拿他有什么办法?设计师嘛!”
这是他在暗示我的装束太随便:只穿一件短袖汗衫和一条运动裤。
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并想为自己辩解一下,说是太匆忙了,没来得及换衣服……
斯大林这时打断我的话说道:“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也想这样,只是职位不允许而已。”
快要落山的太阳把办公室照得格外明亮。斯大林象往常一样,从写字台到门口来回地踱着,仔细地在听别人讲话。
我靠在桌子边上,面朝他站着。阳光照得我睁不开眼,我不由地眯起眼睛。
斯大林看到这个情况,便走过去放下了窗帘。
“现在好些了吧?”他问道。
“谢谢,斯大林同志。”
“谢什么,早就该讲话嘛。”
几天之后,我又被召到斯大林那儿去了一趟。莫洛托夫也在他那里。
谈完公事之后,我便起身说道:“我可以离开了吗? 斯大林同志。”
“您有急事吗? 坐下吧! 喝茶吗?”
勤务人员端上三杯柠檬茶,并给斯大林单独一碟切成两半的柠檬,他挤了一半放入自己的杯子里。
“嗯,情况怎么样? 莫斯科有什么新闻?”
斯大林当时的情绪很好,也很和气,看来他是想休息一下,稍微摆脱一下日常事务,随便聊聊议程以外的话。
我和其他许多莫斯科居民一样,当时对莫斯科市苏维埃决定毁去环城公园的花木感到愤慨。莫斯科非常漂亮的一些街心花园,其中包括具有历史意义的、长满古老菩提树的诺温斯基街心花园,都给无情地砍个精光。环绕市中心的环城公园好几公里长的大片绿化地带的花木统统被连根挖掉,并灌上了沥青。
当时传说纷纭,似乎连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也将遭到同样命运。看来这是谈这个问题的最好机会。于是,我就说道:“据我看来,目前大家最关切的问题之一,就是毁坏环城公园的林荫道。莫斯科的居民对此很不满意,都绞尽脑汁地想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流传着许多谣言和说法……”
“那么,都说些什么啦?” 斯大林警觉地问道。
“有的说,这样做是为了使部队和坦克在打仗时能更方便地穿过城市,有的说,一旦打仗遭到毒气进攻时,树木会使毒气聚集不散,还有的说,是因为斯大林不喜欢花草树木,所以他指示去掉街心花园。”
“简直胡说八道! 谁说是根据我的命令?”
“许多人都在说。”
“那么,是真的喽?”
“是的,就在前不久,我曾到莫斯科建筑施工部门一位领导人那里去过一趟,责备他砍去树木是不对的。他自己也感到愤慨,并说这是根据您在讨论莫斯科改建计划时所给的指示进行的。一句话,是根据‘斯大林的计划’。”
斯大林愤怒地说道:“我们对任何人都没发过这样的指示! 只谈过要整顿街道秩序,并把那些不是美化而是有损市容和妨碍交通的枯萎树木清除掉。”
“您看,只要您一提什么事,就有人心甘情愿卖力气,而且把上百年的菩提树也给砍掉了。”
尽管斯大林已明显地感到不痛快,我还是没能忍住话头,问道:“那么,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怎么办?”
“没听说过。您从哪儿得到这些情况的?”他问道。
“大家都这么说……”
“我想还不至于这样吧。怎么样? 莫洛托夫,我们不会欺侮特维尔斯基街心花园吧?” 斯大林微笑着说。
斯大林默不作声地喝完了自己杯子里的茶,便递给我一张纸条看,手里拿着铅笔,显然想解释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
原来在讨论莫斯科改建计划时,斯大林说他曾经去过第一梅珊斯基街,他认为这条街是绿化搞得不好的典型。第一梅珊斯基街(现在叫和平大街)本身并不太宽,可是两边却留着布满枯树的草畦。这些草畦使车行道变得很窄,人行道也没美化,整条街都很难看,因为草畦上的草都被踏死了,灌木丛的树皮也被剥掉了。
“我说这些的目的,”斯大林继续说道,“是为了今后不要把整顿莫斯科街道理解为这样的‘绿化’——然而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却是根据自己的意见去解释,而且是按照‘强迫傻瓜崇拜上帝,必然要碰得头破血流’的谚语行事。”
“莫洛托夫,你瞧瞧! 人家干的任何蠢事,责任全都推在我们头上了,真是诿过于人,”斯大林嘲笑地说。
有一次,找到一个合适机会,莫洛托夫也在场,在研究完航空业务问题之后,我便决定找斯大林谈谈自己对建设问题的想法。当时我对我们新设计局和装配车间的建设问题很有看法。大家对官僚主义作风深感痛心,必须在建设过程中加以克服。
我列举了我们建筑部门因循守旧的一些例子,特别谈到那些以规范、标准和各种规章制度为借口而制造的种种障碍。一方面说有标准,然而与此同时,每个建筑施工部门又要把一切东西,乃至窗户插销和门把手,全部从头到尾重新设计一遍。
“他们对每一件小事都要干预,使人寸步难行,甚至还引证了一些建筑法规,”我抱怨说,“然而我希望赶紧把我们设计局建起来,而且不能次于西方。”
“那您就别听他们的,如果您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话。您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怎样做吧!”
“哪能不听啊,人家不给建怎么办!”
“很简单,您就说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决定的。”
“谁会相信这个?”
“那就让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核对,我们会给您作证。”
我还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情。一次我又被叫到斯大林那里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
斯大林说:“事情非常紧急,必须很快完成。需要什么帮助吗?”
我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具备各种条件去完成任务。”
“那很好,如果将来需要什么,那就不要客气,打电话或者来找我帮助都行。”
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我说道:“斯大林同志,我有一个请求! 不过这是件小事,不知道值不值得麻烦您?”
“说吧!”
“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需要经常到机场去。可是,我们厂汽车不好使。我需要两辆‘埃姆—1’型小汽车。”
“还要别的东西吗? 只要两辆汽车?”
“是的,再不要别的东西了。”
我从克里姆林宫回到工厂。我的副手一见到我就说:“汽车与拖拉机工业人民委员部刚才来了电话,要我们派人带封介绍信去领两辆‘埃姆—1’型小汽车。”
他让我在介绍信上签了字。第二天两辆崭新的“埃姆—1”型小汽车就已停在工厂的车库了。
傍晚,党中央委员会打来电话,问是否已领到汽车。这是在检查汽车与拖拉机工业人民委员部是否执行了指示。
1939年,我在总主教池塘的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大楼得到一套新的住宅。设计师伊留申和波里卡尔波夫也迁到了那里。
楼房是新建的,但只给波里卡尔波夫装了电话。斯大林好几次来电话,都是由波里卡尔波夫家的人来叫我去接的。他家住在楼下,我感到非常不方便。
所以有一次,波里卡尔波夫家的女工作人员跑来说,让我马上给波斯克列贝舍夫,也就是给斯大林去个电话。
我为了不妨碍波里卡尔波夫起见,便到附近商店去打公用电话。
在谈话时,斯大林问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不接电话。
我解释说,我是打的公用电话。
他感到诧异地说:“怎么,您家里没有装电话?”
第二天晚上,当我下班回到家时,看到我的屋子里已经装上一部市内电话。
不过,这事到此还没终结。
不久,一次在电话里,斯大林想了解有关新飞机军械的某些详细情况,并提出了问题。
我拒绝回答,我说道:“斯大林同志,我不能跟您谈这个问题。”
“为什么?”
“这些问题是禁止在市内电话上讨论的。”
“哎呀! 对,我忘了! 怎么,您家里没有直通电话?”
“是因为按级别才没装吧?”斯大林笑着说道,“那好吧,晚安!”
和上一次完全一样,第二天我发现写字台的市内电话旁又装了一部电话机。这是政府机关用的电话,叫做“转盘”式。之所以叫“转盘”式,是因为当时莫斯科的市内电话都是手摇式,也就是说得向中心电话交换台说出号码。而克里姆林宫则装的是莫斯科第一个自动电话交换台。政府的这种电话交换台的号码数量有限,打电话时,使用者就象现在打电话一样,每次拨动号码盘就行了,因此取名为“转盘”式,后来又把这种电话称作“克里姆林”式。
1939年12月末。斯大林的情绪很好,又开玩笑,又说笑话,在办公室里来回走着,吮着已经熄灭的烟斗。
“年轻人,您多大岁数了?”
“三十三岁了,斯大林同志。”
“多大?三十个蚜虫? 这很好。”他这样开玩笑,是想故意强调我还是“孩提时期。”
他装满烟斗然后点着,便严肃地停在我的面前说道:“您是共产党员吗?”
“是的,斯大林同志。”
“是党员就很好……”
接着他又开始踱来踱去,若有所思地重复着:“很好,很好……”
很快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天晚上斯大林要了解我的年龄和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