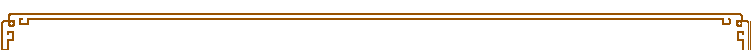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
您可知道,我们是以多么欣喜和骄傲的心情,关注着列宁格勒的伟大斗争!每个最不引人注目,最最微小的有关你们英勇事迹的消息,都激动着所有真正的爱国者。关于你们列宁格勒人流传着各种神话,我毫不怀疑,这些神话将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应该承认,我羡慕你们,深悔处在后方。当然,我也正为胜利贡献出一切力量,不停地工作。以后将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伟大的战争中也作出了努力,是十分愉快的。有个好消息告诉您,我终于获得了出差的机会,希望在20 日左右能当面向您表示我喜悦的心情和紧握您的手。
指望得到您殷勤的邀请,住在您处:当然,这要看是否方便,至于食物,我将尽我所能,给您带去。
请再一次接受我竭诚的祝贺。再见。
敬仰您的马尔采夫
国家安全局中校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某个曲子的节拍,看着他面前的信出神。它刚从化验室里拿来。经过最细心的检查没有发现任何有意思的东西。
这只是一封从“大后方”寄给列宁格勒人的普通信件。
他再一次仔细地读了读信,背靠到椅背上。”难道是复杂的密码?”他想。
信是今天早晨,从十字岛附近拘留的那个人的皮夹子垦找到的。里边另外还有一些证件。看来德国人11 月7 日夜里,用拖船把小船从彼得戈夫拖到航线上,然后那个人自己摇船到小涅瓦河河口。这封庸一定有着某种特别的意义。
肃反人员的”第六感官”提醒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随着这个“敬仰者”的到来,将开始一场重大的战斗。在他到来的当天捕获马尔采夫当然毫不费力,但这不解决问题。在马尔采夫背后无疑还有人,并且还不清楚他来列宁格勒有什么目的。
前线的情况要求苏联的反间谍机关深入、精确又迅速地工作。法西斯分子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们已经感到,列宁格勒站稳了脚跟了,正在准备反攻。
如果他手里握着线头,应该就此理清整个线团。
信是写给一个在城里深受人们尊敬的学者——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灭洛夫的。他是个化学家、社会活动家,工作在国防工厂里。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得越多,这封初看简单的信越发变得是个谜。几十种各式各样似乎很正确的推测在头脑中闪过,但它们都站不住脚。他当然没有打算在书桌旁边解开疑团:但是他喜欢着手侦查以前,先为复杂的问题绞尽脑汁。这样做以后事情有个头绪,真相大白了,再来检查自己当初的想法和推测是很有益的。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了张纸,做了几个记号,把它藏到桌子边上的抽屉里,接着挂了个年线电话。
“布拉科夫同志吗?您那儿全部准备好了吗?我马上就来。”后来他拨了个市里公用电话号码,一会儿传来了个女人响亮的声音。
“您拨的那个号码听着呢,”
“什么‘号码’?马戏团的还是杂技团的座位号码?”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玩笑问。
“我是值日人员,同志。您要找谁,我没有空开玩笑。”
“对不起,我没注意到您紧皱着眉头。请告诉我,什么时候能见到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
“任何时候都可以……除了夜里。”
“确切点,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从早上8 点,到晚上10点,你是谁?科利亚吗?”
“不是科利亚。”
“是吧!我一下子听出是您,明天晚上您做什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挂掉了听筒。“寂寞了,可怜的人,在节日值班,”他带着一丝冷笑想。
他把皮夹千里的东西:公民证、粮票、信和拘留的记录,放进文件夹内,看了看表,走出办公室。
预审员的房间里,除了等候着的助手,还坐着女记录员,她正在削铅笔。
中校走进来,两人都站了起来。
“您好,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对不起,不得不在今天扫”扰您,”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伸着手,微笑着说。
“哪儿的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老实说,我自己也希望今天休息一下,可是没有办法布拉科夫有所等待地望着首长。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文件里抽出信来,把它藏进桌子的抽屉里,其余的都摊在桌上。
“怎么样,我们这就开始审问,”他对助手说,”您先开始,我看看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拉科夫走出去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椅子搬到了暗角落里。他在那里别人看不见,放在桌上的灯光被反射镜反射着,照亮了房间的中央。左边小桌后,坐着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
“我们会工作得很久吗?”她问。
“恐怕会很久,事情很紧急。斯拉维克近来怎样?”甚至在黑暗里也看得很清楚,女记录员高兴得脸红了。
“谢谢您,很健康。现在改行了,决定当坦克手,用小盒子制造坦克是他唯一的职业……”被捕的人走进来,谈话便停止了。
“坐到这儿,”布拉科夫说。
那人坐到指定的椅子上,架起了腿”两手插进口袋:儿乎就在同时,他又换了个姿势,放下了脚,两手叉在胸前。接着他又重新把两手伸进口袋。
布拉科夫坐到桌于后面,不慌不忙地拿出了烟盒、打火机,点上了烟。您姓什么?”他从一般问题开始问起。
“卡扎稗夫。”
“名字和父名。”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
“生在哪年?”
“1901年。”
“出生在哪里?”
“萨马拉附近。”
“准确点。”
“马克西莫夫卡。”
“民族?”
“俄罗斯人。”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觉得布拉科夫有点慌张,但举止很得体,提问镇静自若。被捕的人无精打彩,回答问题很冷淡,大概,他意料到自己的命运会有这样的转变,事先就准备了逆来顺受,“他知道自己干的事情,”中校断定。
“战前您住在哪儿?”
“在列宁格勒。”
“怎样迁来列宁格勒的?”
“说来话长。”
“不要紧,我们有的是时间。”
“来学习,于是一直住了下来。”
“请说详细点。”
被捕的人开始叙述,他怎样在革命的头几年来到波得格勒学习。打开了一个普通人的自传,活着没有特别的志向、爱好和思想,过一天算一夭。在这种生活中也有乐趣。被捕的人显然很乐意回忆这段生活。总的看来,他说的是实话。但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话顿住了。
“战前您在哪儿工作?”
“还在列宁格勒呗。”
“动员您去军队了吗?”
“没有。我患有暗疾,有凭证兔服兵役。”布拉科夫抬起了头,仔细打量了一下被捕的人;但那人低头坐着,对这个一点都没有注意。
“您生什么病?”布拉科夫又用先前的语调问。
“我也不大清楚。”
“怎么您连自己的病也不清楚?那总不至于吧。”
“至于也罢,不至于也罢,反正您不会相信!”被捕的人突然生气他说。
“为什么不相信?相反,我相信您说的一切,不过为了使审判员也相信,我想把一些问题弄明白。如果您认为,预审员关心的是把您没有犯峋罪行妄加在您的身上,那就错了。我们关心的只是一点——知道事实。如果您也右这个愿望,那末,我们的利害是相一致的。”记录员斜视了一眼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用手掩住了口。中校明白她笑的原因,布拉科夫甚至在声调上也在摹仿他,他自己却并未意识到。“如果您不想讲,”布拉科夫声色俱厉地继续说,”那是您的事,但到那时纸上一片空白,用什么来填满它呢?不管怎样,您必须回答所有问题。至于您的病将由医生们来查明,他们会确定您生的究竟是什么病。余下的几个问题要弄弄清楚,昨天清早,您在小涅瓦河被拘留,是这样吗?”
“是。”
“您在那儿干什么?”
“捕鱼。”
“捕什么鱼?”
“碰到什么捕什么呗。”
“捕到了什么没有?”
“还没有来得及,我刚刚到那儿。”
“为什么您丢弃船,想躲起来?”
“害怕了。”
“怕什么?”
“怕会弄不明白,就逮捕起来。战争时期嘛。”
“皮夹怎样会落到水里的?”
“为了拿证件,我把它掏了出来,我正要爬上快艇,船恰好摇晃了一下,于是就掉了下去。”
“哪儿借的船?”
“朋友那儿。”
“他姓什么?”
被捕的人思索一下,痛苦地说:“多说什么?反正您不相信我。”
“您这人真怪,我不是对您说过了:相信。万一有什么误会,把您拘留了,应该全都讲清楚。借给您船的那个同志姓什么?”
“我什么也不讲了,您会把我朋友也关起来的。”
“为什么?”
“那你们为什么把我关了起来?”
审问拖延了。
这时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个人了解了,明白卡扎科夫没有被动员去军队,因为关在监狱星,这点卡扎科夫自己后来也吐露了出来,“暗疾”和”有凭证兔役”是典型的监狱黑话。如果他不知不觉使用了这些黑话,那就说明他在监狱里蹲了不少时间,奇怪的是布拉科夫没有利用这一语漏。
“休息会儿,”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站起来说,“娜杰日达·阿尔卡季那芙娜,暂时没有你们的事了。食堂吃饭去吧。”
“您要留在这儿?”布拉科夫问。
“是,我会叫你们的。”助手懂得了首长的话音,一声不响随着女记录员出去了。
为了使被捕的人对他的出现习惯起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室内踱了几圈,接着坐到了布拉科夫的位子上。
被捕的人因为突然干预起先有点惊惶,但很快恢复了常态,好奇仔细地打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原先,由于眩目的灯光那个人没有看见他。
“想抽烟,就请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说,把烟和火柴放到桌子的边上。
被捕的人怄着身子走到桌子跟前,拿了支烟,借个火点上了,然后退到位于上,很过熄地猛吸了口烟。
“谢谢。”
“您当然猜到了,我不是局外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开始慢吞吞他说,“我听了你们的审问,自己在心里想,我们这儿的犯罪者是从哪儿来的呢?要知道,人生下来不会就是犯罪者。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好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幸福。问题究竟在哪里?您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被捕的人警觉他说。
“现在我们两个人单独谈话,也不作任何记录。我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偶然的。俄罗斯有旬老话:‘谁也保不定不坐监牢、不讨饭。’这话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已经过时了,其实是很正确的。经常有些难以预料的事情纠缠在一起,把人搞糊涂了。我们的法律对这个有明确的规定,审判很严,但很公正,法律给犯罪者有弥补过失,回到社会中去的机会。这要靠各人的意志和决心……当您坐在监狱里的时候,难道就不曾想到过这点吗?”
“在这儿?”被捕的人诧异地问。
他这一叫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更肯定了自己的假设。
“不,从前,在战争前,”他确信他说。
“您打哪儿知道的……为什么您认为我坐过牢?”
“因为我有些经验。您可能认为像这样的事只您一个人,错了,您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纳粹分子会利用人的一些弱点为他们服务的。”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着话,没有把眼光从被捕人的脸上移开。卡扎科夫眉间的皱纹逐渐加深着,他深深地吸了口气。可见他在注意地听着,动着脑筋。
“战前您盗用了公款,还是怎么的?”中校问。
“对,是这档子事……盗用了公款。”
“您看,您成了盗用公款的人,那是谁的过错呢?”
“谁也不是……只能怪我自己。”
“既然这样,就该好好回答……您到这房子里来是决意一句话也不讲的。我想,您甚至很乐意去死,是这样吗?”
被捕的人拾起了限度,突然问:”为了活命,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不是在做生意,”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严厉他说,“您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继续拒不招认,这就是把您自己置于最无药救的罪犯行列:一条是说真话,但白承认,老实交代,抵偿部分罪恶。法庭对这点会予以考虑。”
“好,我招,”被捕的人坚决他说。他拍一下自己的膝盖,站了起来,但又立刻觉察到做错了,并且为了掩饰这个不由自主的动作,请求说:”请允许我再抽支烟。”
“抽吧。”他用颤抖的手指拿了烟,擦断了两根火柴才把它点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看了看表。
“想吃点东西吗?”
“现在没有时间顾得上吃东西。”
“为什么?休息即将结束,又要继续审问,得坐上一整夜呢。”
“那好吧,要是可以的话,就吃一点吧。”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拿起了听筒。
“休息可以结束了。女记录员回原位,给卡扎科夫带点吃的来。”
当布拉科夫和女记录员回来的时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靠在椅子上坐着,指头在桌面上敲,他的眼睛高兴得发亮。
布拉科夫知道,首长爱好音乐,兴致高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永远有某个曲调。
被捕的人坐着,弯着腰,头低到胸前,甚至他们进来时,他也没有把头抬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