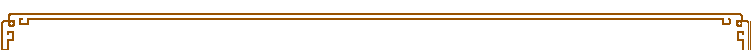康斯但丁·波塔佩奇醒来,但没有立刻意识到在什么地方。暖和、干松、明亮。他盖着的已不是军大衣,而是棉被。睡得很甜。
“我给弄到什么地方来了?”少校用手掌擦着嘴唇想。
摸到刮了胡子的光滑皮肤,一切立刻都记了起来。在作客!昨天他好像从“大后方”来到了列宁格勒,冒名马尔采夫逗留在一个认识的化学家家里。
他究竟叫什么名字?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主人本人出差去了,这儿住着的是他的孩子:科利亚和阿利娅。晚上他去了澡堂,后来刮了胡子,8 点左右就躺下睡觉了。
现在几点了呢?
康斯但丁·波塔佩奇从挂在椅子上的上衣口袋里拿出了手表,看了看。
“哎呀,我的天!11点钟了!我究竟睡了多少时间,16个钟点。”该起床了。他得到批准可以休息到明天,应当享受一下,可以再躺上一、两个钟点,被窝里又暖和又舒适。
住宅里一片寂静,没有一点声息,要知道他在这儿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躺在床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劝他与孩子们住上两天,给他们举行个类似考试的检查,看看他们当他在的时候表现怎样。
“那又怎样?目前一切都很好,”少校想,“迎接我很沉着,又很热情:
不慌张,不忙乱。科利亚带我去了澡堂,就去学校里了:阿利娅晚上把我灌饱了茶。是个好孩子。独立自主、关怀备至。真是个女管家。假如我的女儿像这样就好了,”康斯但了·波塔佩奇心里想,他不由把阿利娅同自己娇宠惯了的女儿作比较,他女儿十分任性,什么也不会做,还什么也不想做。现在她跟学校撤退了,住在乌拉尔,“她在那儿不知怎样?”米沙早就坐在那儿读书。眼睛在一行行字上溜过,但对所读过的一个字也没有记住。房门虚掩着,他努力倾听,为了不放过客人起床时的一举一动。
他到底能睡多少时候?
时间令人难受地延续着,终于门嘎吱一声响了,只听见一阵沙沙的脚步声。客人进了浴室,清楚地传来哗哗的水声和粗重的擤鼻声。
“他在房间里做了些什么,怎么穿的衣服,这些都没法听到,”米沙想,“应该使他的房门关不紧,把铰链拆坏,还是另想别法?”几分钟后传来了说话声。
“有谁在家吗?”
“有!”米沙走到前厅去,答应道。
“这么静,我真以为你们都走了……丢下我一个。海员你好,学校里怎么样?”
“没什么,”米沙与客人道过好,镇静地回答,“客厅里坐,格里戈里·彼德罗维奇,阿利娅在那里留下了早饭。
您睡了很久。”
“是……我自己也奇怪,睡了16个钟头……像只土拨鼠。”他们进了客厅。桌上放着把茶壶,套着个半新不旧、装饰鲜艳的棉布套:
没有切开的面包和罐头香肠整整齐齐搁在碟子里。
“瞧,她考虑得多周到,”客人说,“可爱的女管家……您得为您的妹妹自豪!科利亚。那她本人在哪儿?”
“在学校里。大概冷了,”米沙拿起套子,摸了摸茶壶,说。
“没关系,没关系!”客人劝止他说,“我不喝很热的茶。据说茶热会闹肚子:溃疡、结肠炎……您注意过没有?科利亚,动物都不喝和不吃热的。
譬如,猫、狗。”
“是,这我看到过。”
“就是这样。猫在吃热鱼热肉的时候很怪。先用爪子试试,滚动几下,等它冷掉再吃。那为什么?要知道谁也没有教它们……这是天性。天性是件了不起的事。人类脱离了天性,因此就有许多麻烦事,”客人给自己倒了杯茶,坐到桌子边,继续说,“牙齿先坏,其次眼睛,然后头发掉了……秃头的人多么多!关于疾病我就不必讲了……全邻关键在于脱离了天性……”米沙就像头一次一样,将信将疑听了马尔采夫所说的一切。不知怎的,他觉得敌人说的和想的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
“多狡猾!为了骗取信任,尽说些有道理的东西。”他想。
关于天性的说法对米沙来说不是什么新消息,尼古拉.瓦西里那维奇也爱讲天性,主张凡事不能过度。
“科利亚,你们这儿电车线路与从前一样吗?”客人问,“还是那几条线路吗?”
“是……”米沙不很有把握地回答,“能通车的地方都通车。”
“那么什么地方能通车呢?”
“大概不太危险的地方。往西和往北的线路与从前一样通车,而往东……
我就不清楚了……那儿是前线。”
“明白了。我要出去一趟,与几个人碰碰头。”
“去哪儿?”客人仔细看了看少年。米沙似乎觉得,那人的眼睛这时亮了一下,不知是他觉着可笑,还是生气了。
“如果您需要,我可以领路,”米沙提出,“您对城市不熟悉。”
“怎么会不熟悉?列宁格勒我来过好几次了。”
“可为什么不来我们这里呢?爸爸说您在休养所时就打算来了。”
“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客人逃避直接回答,“最好说说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他工作很重吗?”
“是,工作很重。他目前正在发明一种信管什么的。”
“这很好。”
“当然不坏。意外的礼物会使法西斯分子哭叫起来,”米沙幸灾乐祸他说,但是他觉得这还不够,又补充说:“这样的礼物给他们准备了许多……
为了不让他们惹事生非,下次再来纠缠我们。”“我看得出,您很生法西斯分子的气,”客人露出一丝冷笑说。
“当然生气……我已经不是小孩了。多少懂得一点。我们没有触犯他们,对吗?他们却像强盗似地闯进来……现在大概倒霉了,闯进来了,但碰得头破血流……”讲到法西斯分子,米沙沉不住气了,不再隐瞒他的仇恨了。是的,这怎能忍得住!母亲的牺牲,父亲的受伤,狂轰滥炸,残酷的包围、饥饿……所有这一切都想提醒马尔采夫。让他知道惩罚的日子到了,没有什么可哀泣和叫苦的了。
“自食其果。”听着日益强大和雷霆万钧的苏联炮声,瑟索耶夫总喜欢说这句话。
“是呀……闯进来了,但碰得头破血流,”客人沉思地重复说,”战争的转折点已经十分明显……我想,很快我们战线上就要开始进攻了。”
“我们什么战线上?”米沙大吃一惊。
“我们列宁格勒战线上,”客人解释说。
米沙谨慎起来。马尔采夫的回答使他十分为难。
“他说的是谁?这怎么理解,难道法西斯分子准备袭击列宁格勒吗?也可能指的是苏联军队,但是他说,”我们战线上’。”
“谢谢,科利亚,”客人从桌边站起来道谢说,“现在我要去个地方,晚上回来。”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我怕您碰下到我们,先给您钥匙。”
“太好了!”
“一般来说,晚上阿利娅在家。但说不定会去商店或者其它什么地方。”拿到了钥匙,客人又一次谢过了“年轻的主人”,往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米沙留在客厅里,急不可待地瞅着电话,他想,应尽可能快地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个电话,告诉他新的消息。
等不很久,马尔采夫低声哼着歌,到前厅里去了,听见他穿上了衣服,咕哝着什么,又是咳嗽,又是大声喘气。最后,通户外的门卡嗒一声扣上了。
米沙躲在窗帏后面观察着。马尔采夫在院子里出现了。笨拙地跨过一堆堆砖块……走了。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在他的办公室里。
“万尼亚叔叔,这是我……科利亚。当然走了,我看他走过了院子。他睡了很久,将近12点起床的。穿了衣服,洗了脸,吃了早饭。我们谈过话。布拉科夫关于那个瓦夏告诉您了没有?……不,这是我昨天知道的,今天是另外一件事。他说,法西斯分子准备在列宁格勒战线上进攻……不,这是我自己作出的结论,他说‘我们战线上’。‘我们’!万尼亚叔叔,他不是法西斯分子吗……那未是什么?可见很明显,是他们的战线。他是确叨这么说的:‘我想,很快我们战线上就要开始进攻了……’好,您自己作结论吧……现在走了。往哪儿?没有说。我提议,如果他对列宁格勒不熟悉,我可以带路,他说这里来过好多次了。问起了爸爸,谈到了天性……就是关于喝热茶是有害的。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教师!……没有,我跟他没有争论。现在完了……昨天我学校里没有去,在瓦西卡·科茹赫那里。他在病院里……怎么为什么?不然我就得考两分。真的!她开始口授一句无关紧要的,但很伤脑筋的句子。我们星期二两堂课只弄了一句。我会背诵。‘在路上迎面碰到几辆街头马车,但是这样破旧,仅能载马车夫,叔叔只在特殊情况下和重大的节日里才用它。’”
米沙说完,听见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笑声后自己也笑起来了。“不,真的!这儿是大炮、飞机、坦克,而她老是一套关于马车夫,语法中的各种例外……我懂得,万尼亚叔叔,今天我去……阿利娅不在。她一点也不慌张,开头我也害怕。女孩子们,她们比我们男孩子滑头,突然间却比我们要好……确实的!这是我从学校里知道的。不,真的,万尼亚叔叔。如果女孩子撤谎,绝对不会知道,她连眼睛也不眨一眨……她说电话里谈话很危险,可能有人偷听。我解释过这不是一般的电话,这儿城里有地下电缆,无论如何偷听不了……什么?就在车站上,当然可以……是!”
与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谈过话后,情绪安定了,米沙又高高兴兴地读起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