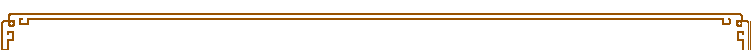短短的白天快过去了。街上还很亮,但不久前在城市上空升起的银白色烟幕已经扩散到空气中,与灰色的云雾溶成一片。再不久,就会什么也看不见了。
“为什么放起烟幕来?”列娜急速地往家里走,担心地想,“难道防御空袭吗?”
每当收音机里响起了预告德国飞机临近的警报声时,不知为什么恐怖笼罩了列娜。她捂住了耳朵,跑进里屋。好像仅仅为了不听见这个声音,她准备从五层楼的窗子里跳下去。叫声停止了,扩音器里开始响起了滴嗒滴嗒的节拍计声,列娜就很快安了心。为什么警报声对她产生这样的影响,连她自己也不明白。高射炮的射击,炸弹或炮弹的爆炸虽然使她颤抖:但心脏没有因为恐惧而感到受压抑。就是这个悲惨的、讨厌的叫声对她产生恐怖的作用。
房屋的大门边站着米沙。
“为什么你耽搁这么久?”他不满地问。
“我们开了班会。”
“得关照一声……”
“我自己也不知道会那么久。”
“这还是不成理由。你自己知道……炮轰……一般来说……等着你,就产生各种想法……”
“好啦,科利亚,说真话,我确实不知道会耽搁那么久,”列娜温和地微笑着说。她明白米沙为她不安,而这是很愉快的。
“打个电话。你们学校里有电话吗?”
“大概有。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在家吗?”
“不在家。我走了,阿利娅,不然要迟到了。”
“干么把香肠挂起来……”列娜朝上看了看说。
“就让它挂着……阿利娅,今天给我们拿来了唱机,因此你得注意。”
“为什么要唱机?”
“大概需要。我把它放在衣橱里,如果马尔采夫偶然看到问,就说我们以前就有的。”
“他不会问。”
“当然他不会钻进衣橱里……但也说不定有这可能。”
“唱片呢?”
“唱片也拿来了。”
“什么唱片?听听可以吗?”
“暂时不必,以后一起听……那么我走了!”
作业布置很少。列娜走遍了整个住宅,想寻样事做;一切收拾好了,都很妥贴。顺便她往衣橱里张望了一下,那儿真的放着一只红色的小箱予,旁边有只装唱片的盒子。列娜开亮了前厅的灯,蹲到开着的衣橱里,用脚抵住门,开始翻看唱片。这儿既有严肃的乐曲,也有一般歌曲:有抒情歌,也有各种舞曲。她把唱片放成四叠,身子一直往里移,到后来背脊碰到了橱壁。
再也没法用脚去抵住门,只得把脚也收进了橱,那门呀地一声轻轻地顺势关上了。
就在这时她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个大胆的计划。”为什么不呢?如果躲在这个衣橱里,看看马尔采夫趁谁也不在家的时候做些什么?会不会给什么人打电话?或者与谁谈话?”列娜很快收起了唱片,把它们放回原地方,察看了一下农橱。橱很大,很宽敞……这里即使藏进十个人也行。为了尝试一下,她钻到衣橱里,弯着膝盖蹲下去。门呀地自己关上了。黑暗、暖和,她甚至觉得很舒适。闻到一点樟脑味和勉强可以察觉的一种什么香水味。
“应该告诉米沙!”满意于自己发现的列娜决定了。
康斯坦了·波塔佩奇回到扎维亚洛夫的住宅里,为了跟孩子们告别,对他们说几句临别赠言,拿走自己的箱子。考验完了,晚上应该向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报告,说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孩子们的举止很自然得体、沉着镇定,绝对胜任得了任务。
走进院子,停在一堆堆的砖块前面,他望了望住宅的窗子。他觉得有个淡淡的、刚刚可以看得出的光影在最边上一扇窗上掠过。这是当附近有谁走过,他的阴影映在玻璃上时常有的。
“家里有什么人在,”卡位特金断定说,“很可能是阿利娅。”
登上楼梯,揿了门铃,他在门前站了好久,等着有人给他开门。铃声很响,即使在厨房里也听得很清楚。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想起他口袋里有住宅的钥匙,就自己开了门。
“阿利奴!是我!”他开亮前厅的灯,喊道,“阿利娅!”一片寂静。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走遍了所有房间,开亮了各处的灯,又回到了前厅。
住宅里什么人也没有。奇怪,难道窗上掠过的光影是外面的反照吗了阿利娅的大衣没有佳在衣架上,但是蓝色的软帽放在原地方。假使没有窗上的光影。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可能不会注意到软帽了……
现在一切全明白了。她在家,并为什么藏了起来。
“还是垮了!”卡拉特金惋惜地想,”想给这场考试打五分,而现在将得个一分。”但她能躲在什么地方呢?床底下吗?桌底下吗?窗帷后面吗?
对这个问题不得不思考了很久。在前厅里放着只衣橱,它的门关得不很紧。康斯但丁·波塔佩奇走近衣橱,推上门,锁了起来。
“啊哈,小鸟不要动,抓住你了,别从网里飞掉……”当锁刚卡嘈一声锁上,他就记起了这只古老的童谣。他等待了一会儿。
她会怎么办?自个儿请求把衣橱打开,并开始为自己申辩。
一分钟,二分钟,三分钟……过去了。毫无动静。康斯但丁·波塔佩奇把耳朵贴在橱门上,屏息着气。不,他显然没有弄错,衣橱里蹲着个人。耳朵里清楚地听得抑制的呼吸声和既不像纸张,又不似衣料发出的轻微的瑟索声。
他关了前厅的灯,走进客厅,埋在沙发里,在黑暗里坐了一会,考虑着造成的情况。
下去该怎么办?毫无疑义,阿利娅躲在橱里,但是她藏到那里是否出于她的本意呢?很可能这是米沙的想法,那就应该教训他们两人。但是怎么办?
在她哥哥未回来之前不要放她,以后给他们洗洗脑筋,或者吓吓她,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未经深恩熟虑的自作主张会导致什么结果……
时间在过去,许多种各式各样的方案在脑子里转:但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觉得它们都不合乎教育原理,不足以说服人。最后,无法可想了,他决定通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那是他的作战计划,让他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列娜蹲在衣橱里,缩作一团,尽量不出声。她随时等着马尔采夫开门,发现她。
那时该怎么办?说些什么?
不错,她稍迟才想到这些,那时马尔采夫已去客厅里了。在橱门突然嘎吱一声关紧,钥匙在锁孔里转动时,她吓得根本什么也不能考虑了。
现在她听见,他怎样拨了电话号码,后来又怎样挂了听筒,去到自己的房间里,没法听到他在他的房间内做了些什么:但很快又响起了脚步声,并且十分近。
列娜吓呆了。马尔采夫把样什么东西放在前厅的地板上,来回走了一会……突然砰地一声响起了通户外的门。
走了!
列娜静听了大约一分钟,后来站起来,试着打开门:但毫无结果,锁得很牢,把门打破需要很大的力气。列娜断绝了想出来的念头,坐到原先的地方。
“干么我爬到了这儿?为什么下跟米沙商量一下?要知道开头我曾这样想过的。”列娜明自作了蠢事,但心里不知为什么没有后悔。
她挑选着唱机的唱片,想出了这个计划,激动得好久不能安静。站在厨房的窗边,直到天暗下,老是想,想……后来回忆起了个勇敢的男孩子的英勇行为。他有着个怪姓一科茹赫。瓦夏·科茹赫。昨天米沙谈到了他。就一切看来,米沙不但为他可惜,而且羡慕他。那又有什么?这完全可理解。她自己也有点羡慕,从头到脚缠了绷带的,受伤的人她在军医院里见过;因此她不难想象瓦西卡躺在床上的样子。
这时候有人走进了院子里,列娜立即猜到了这是马尔采夫。
其余一切发生得都违背她本意。应该行动,着手做点什么事,如何表现一下自己。“藏起来!”脑子里闪过了一个思想,而脚自动地挪到了前厅。
她抓起了大衣,把它丢进了橱里,奔去拿了放着教科书的皮包,就钻到了里面,随手尽可能紧地关上了门,差点没把指甲折断。
她就这样在橱里了,因此心里没有意识到错。似乎她藏进那儿并不出于自己的本意。
随着夜幕的降临,走在街上是很危险的。路上可能撞着迎面的行人。这种相撞往往撞得鼻青眼肿。
这时“小萤火虫”就帮了忙。
战前不久,某个有进取心的手工业合作社生产了一批样子像大钮扣似的,嵌了相片的胸针。胸针很为大家喜爱。列宁格功也开始出现胸前别着各种像片的人。胸针的销路鼓舞了这个合作社。它显然认定,这个时髦会普及到国内每个居民,于是开始大量储备胸针:但这时就像经常发生的一样,一当胸针在所有的商店和铺子里出售,人们对它的兴趣消减了。时髦过去了。
但胸什剩了下来。它们放在仓库里被遗忘了,谁也不需要……然而这时又用上了。代替相片。胸针的表面涂了发光粉予以出售。现在列宁格勒人很乐意购买。人们胸前别了”小萤火虫”,在一片黑暗的街道上迅速地走。
米沙有个自制的,然而是“艺术化的小萤火虫”——发光的兵舰的雕像。
起初他很喜爱,但当其他人身上也出现了锚、快艇、鹿、海鸥等类似的“小萤火虫”时,他不再戴它了。现在他带着“步行虫”电筒,或者就像瓦西卡讲的“厩螫蝇”走。电筒是去年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送给他的,“步行虫”不只用光,而且以声音警告迎面来的人。它的声音也很奇特,啥也不像,有些妇女听了它“嗬吱嗬吱”的声音很害怕。
米沙稳稳地接着开关,一个微弱的,黄色的光点跑在他的前面,照亮了路。这里是熟悉的砖块,那儿是小道……再过一会儿,光点就跳上了楼梯。
“嗬吱,嗬吱,嗬吱……”电筒的好处还在于发展手指的肌肉,它还不需要任何电池。真是个手中的小型电站。
米沙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住宅的门,一进去就立刻感到有些不对头——又暗又静。在开亮前厅的灯时,他还希望这是错觉,但当他看到了空空的挂衣架时,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模糊的不安。米沙未脱衣服就进了马尔采夫的房间,打开了电灯开关,他发现,白天还搁在桌子和椅子上的书本、衣服、肥皂没有了,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走了,不来了?”
米沙快步走进了列娜黑洞洞的房间,激动地开了灯,里面阒无一人,所有东西都照原先一样放着,一点怀疑的东西也看不出。她究竟能去哪儿呢?
他们顶先约好,如果突然离开,互相留下纸条……可是无论在厨房里,自己的房间内,还是客厅中,他都没有找到纸条或可说明这种情况古怪的任何其它东西;但是最令人不解和担心的是不见了马尔采夫的行李。
“他猜到自己上了当,跑了,或者已经逮捕了?”米沙想得愈多,心里愈不安。应该尽快采取个什么办法。但有什么办法呢?用信号叫布拉科夫吗?不,首先该打个电话,该得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指示。
米沙拨了个电话号码,长时间地听着话筒里拖长的铃声,急不可待地变换着两脚。
“难道办公室里没有人?不是应该有人来接电话的吗?”他懊丧地想。
终于,听筒里传来了弹指声,听见了值日工作人员的声音。
“请叫万尼亚叔叔……火速,”米沙说,就在这时住宅里响起了咚咚的叩打声和闷声的喊叫。
“科利亚……我在这儿。”米沙未听清值日人员回答了他什么,匆忙地低声含糊说了句“我以后打给您”,就挂掉了电话,走到前厅。列娜在屋里,他听见了她的声音:但是她在什么地方呢?
“阿利娅!答应一声!”突然,就在身边的衣橱里,又响起了低沉的声音。
“科利亚!我就在这儿……”打开橱门是两秒钟的事。脸孔通红,满头大汗,一泡眼泪的列娜从衣橱里钻出来。
“啐!我差点没闷死……这么闷!”她喘着气,坐到小凳上,负疚地看着米沙,开始用手绢擦着眼睛和前额。
“我起先不知道谁来了……我以为这是他回来了,”他说,“后来听到了你的声音,我知道了……”
“发生了什么事?阿利娅,谁把你关在橱里了?”
“他。”
“为什么?”
“不知道……他来了,我就躲进了这儿……我想知道他会给谁打电话。”
于是,列娜就毫不隐瞒地、详细地向米沙讲述了,她为什么爬到了衣橱里,怎样被关了起来。
看到列娜活着,没有受到伤害,米沙稍微安心了。当然还得弄明白,马尔采夫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为什么他在离开时把她锁了起来。如果猜到了她躲起来的原因,那么事情就很不妙,必需想个什么办法。
“你可晓得……他走了不来了,”米沙沉思着说。
“怎么不来了?”
“他把自己的所有东西和箱子都拿走了……不过你别不安,目前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这没什么……如果他回来,我们编些什么假话骗他……你想得很好,只是应该在橱里钻几个便于透气的洞……”
随着米沙说话,女孩子的惊恐样子和眼里负疚的神情消失了:而当他赞成她计划的时候,嘴唇上露出了笑容。
“只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明白,他为什么把橱锁上了,”米沙说,”猜到了,还是没有?可能你弄出声了,或者打了喷嚏?”
“哪儿的话,科利亚!我蹲着像只老鼠,很安静……”
“老鼠!老鼠有时也会吱吱吱高声叫起来……乱吵一阵……”
“不,不,他什么也没有听见。”
“那他干吗要谈起未呢?”米沙说,并像船上的老机械师厄古拉·瓦西里那维奇在沉思时习惯的那样,用手擦了擦下颏,“要是他猜到了有人在监视他,就可能跑了。等等……这是你的帽子吗?”
“我的,”列娜说,她的眼里又出现了惊恐的神情。
“就是说,它就这样放着?”
“是……我忘了……”
“现在终于清楚了……根据这顶帽子,任何一个傻瓜都猜得到你在家。你看,落了个这样的结果……你还没有经验。侦察人员他们就像跟地雷打交道的工兵……不能有差错,一不小心,就完了,无法挽回了,”米沙用教训的口吻说。
他喜欢充当经验丰富机智沉着的侦察人员。他看到列娜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么办,光期待他作出某种决定,就故意显得很镇静,脱了衣服,把皮袄挂上了衣架。
“现在喝杯热茶就好了,”他搓着手说,“你以为怎样?阿利娅。”
“弄杯茶要不了多久,只是我没有经受过……我没有心思喝茶。”
“别这样,应该永远做环境的主人,任何时候也不要张惶失错……”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电车上下来,等着卡拉特金,当后者走到他身边时,打亮了电筒。
“沿河岸走,这儿较近,”他阴沉地说,并闷声不响大步走过街道。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并排走着,没有开始谈话。他懂得朋友的心情,打心里同情他。放弃一个经过周密考虑作了充分准备的计划很不容易,但冒险也危险。假如女孩子与“毒蜘蛛”也开这样的玩笑,那断送的不仅是自己和”哥哥”。而是全部计划。
“是呀,不该同孩子们搞在一起,”卡拉特金说,“他们会叫你作难的,万尼亚,以后你会弄得很被动的。”
“阿列克谢耶夫下会,我相信他。”
“你以为躲进橱里偷听这不是他的主意?未必女孩子自己决定得了……”
“我们来赌半打啤酒,”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提议,”如果这是米沙想出来的,啤酒算我的,如果……”
“啤酒我不可惜,万尼亚,“康斯坦丁·波塔佩奇打断他说,“但我不赌,决不!”
“为什么?”
“有这样的说法,两个打赌的人中间,总有一个是傻瓜,一个是坏蛋。我既不想作傻瓜,也不想当坏蛋。”
“不同意。如果这人打赌,又确实知道他会赢,只在那时他才是坏蛋。”
“但你为什么这样相信男孩子呢?”
“因为他已经不是孩子了,这是一;其次,他是个海员,海员是懂得纪律的:最后,我们已经与他工作过,我了解他。”
“我们走着瞧吧,”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不加肯定地嘟囔说。
在屋子的门檐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扯了扯少校的袖子。
“听我说,科斯佳,你还是一个人去看看……我暂时去管理员那里,稍等片刻再来。”
“我看你还是决定冒险?”
“是,应当冒险……但是要有理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小声说,接着就往一边走去。
列娜开了门。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以为她看到他会惊慌失措,但错了。
“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她很高兴他说,“这真巧极了,我与科利亚在喝茶。请靠桌子坐……我们把您的饼干拆开了……味道很好,稍微有点碎……您大概挨冻了!今天是这样讨厌的天气,”在他脱衣服时,女孩子饶舌说。
“喝茶吗,喝茶也可以,”少校同意说,”我今天还要等个朋友。他很快就要来了。”他边走边梳着发进了客厅。米沙坐在桌子旁,对马尔采夫的到来显得很冷淡。
“我给您冲个大杯,”列娜提议说,不等回答就从碗橱里拿出了杯子,“今天我生您的气,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虽然您大概不是有意的。您是不知道……是吗?”
“我不知道什么?”
“不知道我躲在橱里。我以为科利亚来了,就躲了起来……可原来这是您……为什么您把我锁起来?”列娜盯着客人问,“我为您大约在橱里蹲了一个钟头,差点闷死……好得科利亚回来得快。您为什么把我关起来呢?”
米沙好不容易才忍住了笑。马尔采夫的双目睁得像铜铃。他这样惊奇地看着列娜,好像他面前站着的不是个女孩子,而是个什么怪物。
“是的……我似乎真的在离开前锁了衣橱,”他承认,又显得很慌乱地继续说,“但是我不知道您在那里,阿利娅……橱开着门……您自己想想看,为什么您要钻到那里去……”
“我不是对您说了,躲掉科利亚。”
“对……躲掉科利亚!不,这点我脑子里未想到,在你们这个年龄还做小孩游戏……不,我不可能猜到……”
“您真怪!这与小孩游戏有什么关系?我想考验他一下……但问题不在于这儿。这是您的茶,这是饼干。请您别不安,什么可怕的事也没有发生,就是在衣橱里蹲了会儿……我甚至想打破它……谁知它很结实,”列娜不时斜眼看下米沙,活泼地饶着舌。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锁紧了眉头……为什么原来他断定女孩子藏到衣橱里是为了偷听和监视呢?她不还是孩子吗?躲掉哥哥,为了吓唬他,或者就不过是捉迷藏游戏。他是个不高明的教育家,如果连这种极普通的事也分不清的话。
响起了短促的铃声。米沙和列娜带着疑问看了看马尔采夫。
“我去开。这是来找我的,”他从桌子旁站起来说,“我想,他会同我们坐下一块喝杯茶……”马尔采夫开了门,趁来人脱衣服的时候:列娜赶紧准备好了茶,米沙紧张地听着。马尔采夫与来人唠叨着什么,但无法弄清意思。大约两次他听见了列娜和自己的名字,这使他更加警觉起来。新来的客人沉默着。列娜想冲进前厅去,但米沙把她拦住了。
突然,在马尔采夫的伴同下,客厅里进来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这是那样地出乎意外,开头孩子们惊奇得瞪出了眼睛。
“怎么样!没有料到吧?”卡拉特金笑着说。
米沙已经恢复了常态,并毫不慌张地问,“你说没有料到什么?”
“来了这样一位客人,您的老相识……”
“不……您说话真奇怪……这是您的朋友,而我们,比如说,主平还第一次看到他。对吗?阿利娅。”
“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女孩子肯定说。
康斯坦丁·波塔佩奇转向站在门口的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并使了个眼色。
“看见了吗?原来是没有的事……他们第一次看见你。啊呀呀!这说明你骗了我……”
“您这在胡说些什么呀!”米沙埋怨说。
“说我对教授的孩子们很了解,”卡拉特金继续开玩笑说。
“这个我没有对你说,科斯佳,”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走近桌子,终于开始说话了,“我说很了解这个米沙·阿列克谢耶夫和列娜·加芙里洛娃,而教授的孩子只瞥见了一眼。”“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您,意思是……我一点也不明白……”米沙困惑地说。
“立刻会全都明白的……坐下……这是我的茶吗?这个我决不会拒绝。”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坐到桌子边上,把茶杯移到自己的身边说,“应当立即告诉你们,我来的目的是想放弃我们的计划。是,是!放弃并送你们各自回家。但是康斯坦了。波塔佩奇……这个叔叔不叫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也不是马尔采夫;而是康斯坦丁·波塔佩奇·卡拉特金。这是我的老朋友。我请他给你们作次考查……说吧,科斯佳……他们考得怎样?”
“我不是对你说过了……他们表现得很好、很自然。要是没有衣橱这件事,就考五分了。不错,现在解释这是小该子的捉迷藏游戏,这件事上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我要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游戏是不适宜的……不应该玩这种游戏。马尔采夫说不定会想入非非……应该觉得自己长大了。”
“关于这个我已经给她说了。”米沙插嘴说,“现在她全明白了。”
“明白了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眯缝着眼看了看列娜。
“列宁式的实话,明白了!”女孩子尽可能令人信服地把两手放到胸前说。
“我们起先认为,你躲进橱里是为了偷听,”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开口说,“这是个很大的错误。我不是警告过你们,不要自作主张……那根本没有必要。得忘记你们是谁和为什么在这儿!你们只是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的孩子……仅仅是这点!作你们白己的事。你们在这住宅里使我们有可能从近处来监视马尔采夫。看他来干什么,对他进行一下检查……也可能他不是敌人。要知道我们只是怀疑,我们还什么也不知道。假如这是敌人,那就是说,他很小心谨慎、很聪明而且有经验……比方说,康斯坦丁·波塔佩奇一下子就猜到了您在衣橱里……”
“根据帽子吗?”米沙问。
“不只根据帽子,我先在窗里看到了她,”卡拉特金说明。
“衣橱您当然不会再钻进去了,”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继续用平稳的声调说,“但当马尔采夫来的时候可能玩其它什么花样……就是这个使我不安。比如在门后偷听,提个什么问题……”
最后一些话使米沙想起了他与假冒的马尔采夫的谈话,不禁也脸红起来。
“在通常情况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并未注意到米沙的难为情,说,“对一般人来讲,任何这样的问题是客气和关切的表示,而现在这可能被怀疑为纠缠。得让马尔采夫看见,并觉得你们忙得很,正在学习,你们有自己的事。当我在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那里的时候,他叫儿子给我们倒杯茶,科利亚拒绝了。‘我,’他说,’爸爸,没有时间,叫阿利娅。’就走了。”
“这可不好,”康斯坦·波塔佩奇说。
“怎么不好?”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表示不同意见,”如果他确实很忙?
去上课迟了。”“那么阿利娅呢?”列娜问,”她也这样吗?”
“您,阿列奇卡,举止很出色,”卡拉特金说,”真诚、体贴,您就应该这样。只是别再爬进衣橱里,玩些其它的……”
“好,”女孩子低下眼睛小声说。
现在她开始为跟米沙一起想出来的谎话脸红了。不过要知道如果他们承认了,说出真话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肯定会送他们各自回家的,然后把这件事委托给其他什么人。“不,最好让他们真的以为这是捉迷藏。”
“马尔采夫会在20,或21日到来,”伊万·瓦西里那维奇说,”要是可能,我们事先通知你们:但是应该时刻准备着。你们还有时间……习惯起来,演习演习。”
“我们至今名字还叫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米沙承认说,”比如说,有时候她叫我米沙,我叫她列娜。”
“对了,这一切很重要……就让衣橱这件事提醒你们的错误。如果想起了要做什么,先看看衣橱,”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微笑着结束了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