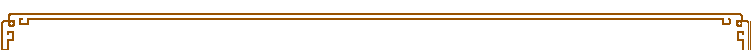每当药房的窗子里出现白色斑点的时候,特里福诺夫睨视了一下他的助手,碰见了满是因惑的目光。
“又一次!她那里出什么事了?”他把望远镜放到眼睛上,咕哝说,“这不是无意的,是某种特别的信号。现在拿走了……”他望着药房的门,但谁也没有从门里出来。
“又挂上去了,”助手抢先说。
“又一次……这已是第5 次了。你注意到还有谁?”
“好像大家都走了,就只剩下带眼镜的男人。”
“是,是……戴芬兰帽,背防毒面具的。”在望远镜里,瓦利娅被看得很清楚。当她回头看着街道的时候,甚至可看清她脸部的表情。有时她微笑着目送正在走过的行人;有时严厉地望着,这时她的嘴唇扰紧闭了起来。
“不再取下来了,可见他在那儿。5 次……为什么要5 次?这不是无意的……你想呀,费佳。”
“我在想,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
“那怎么样?”
“不知道,是个解不开的谜。”
“为什么解不开?有个数目:5 。”
“对于学生来说,‘5’是个好数目……”费佳开玩笑说,“她会不会指的是时间?5 分钟,或者5 点钟,或者过5 个钟点。”
“是个……谜。旦把时间记住,以防万一。5 ?等等,会不会是信号?”
“未必见得……或许5 人……”
“但是他们在哪儿呢?不,十分可能她叫我们集中注意,作好准备……
有什么重要的事……那儿有没有别的出口?或者真的有5 个人……”他们这样坐在窗口作着各种各样的、最难以置信的假设,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站不住脚。谜还是个谜。
好几分钟手帕动也不动地挂在椅子上。
“哎唷……她怎么坐立不安了……”特里福诺夫赶在前头说。
就像回答似的,白点不见了,再一秒钟,药房里走出了个戴眼镜的男人。
“就是他。他在那儿磨蹭了好久……我走了,费佳,”特里福诺夫很快地说,“只是别给他溜掉了……”
这样的天气走到涅瓦大街,特里福诺夫大步走过了架在喷水池上的桥,在街对面看见了个熟悉的身影。戴眼镜的男人绕过水洼,下慌不忙走着。在铸造大街的转角上,他站住了;点了支烟,等电车过去,又继续往前走。街上人不多,跟踪不很困难。离马拉街不远,男人转过身,到了涅瓦大街的另一边。特里福诺夫不得不停下来。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躲到了个防护商店大玻璃不受震荡波和弹片损伤的盛沙箱后面。这时站上正好开出辆电车,男人突然改变了方向,跑了几步,跳上了后面的车厢。
特里福诺夫从隐蔽处出来、生气地目送着远离去的电车。
“给溜掉了!”他惋惜地想,”难道觉察到了有人跟踪他吗?或者只不过像只绕圈子的兔子,以防万一?”可以乘顺路的汽车赶上电车,但是需要特别小心,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对这警告过好几次。倘使间谍开始怀疑到了有人在监视,他们就会想尽方法隐藏起来。那时整个计划就会垮台,还是让他溜了较好。
“会不会他也去公墓上广特里福诺夫回忆起两天前他按瓦利娅的信号跟踪,在尼古拉公墓的亚历山德罗一涅瓦大修道院里不见了那个女人,想,”应该检查一下!”他作出了决定。
特里福诺夫举手拦住了辆军用卡车。
“喂,你干什么?”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粗暴地问。
特里福诺夫从口袋内掏出了服务证,把它拿到驾驶员的鼻尖上,代替了回答。
“去哪里?”他把头缩进驾驶室问。
“渔村。”
“这么说是顺路。上来,伙计。”
“检查员呢?”
“我自己就是……”司机也不经商量,汽车一下子用违禁的速度开动了。
在火车站附近他们赶过了电车,转过弯,沿着旧涅瓦大街飞驰起来。
“很久就吃这行饭了吗?”特里福诺夫问。
“从31年起。干什么?”
“没什么,显然不是新手。”这个称赞使士兵眉开眼笑了。
看到了广场。亚历山德罗一涅瓦大修道院的人口处站着哨兵。这儿驻扎着军队。再一分钟,就出现了仓库的红楼房。
“请刹车,朋友。我下去了。谢谢!”特里福诺夫从驾驶室里跳下来,越过了水沟,在一棵粗大的菩提树旁边停下来。从前尼古拉公墓围着高大的栅栏:但是在封锁的第一年就给人们陆续偷走了,丢在”小铁炉子”里烧掉了。
为了缩短去列宁面粉厂和其它一些工厂的路,许多人横穿公墓,特别在早晨。、尼古拉公墓是列宁格勒最阔气的公墓,这儿风景美丽不是偶然的。
巨大的坟墓建筑、小教堂、纪念碑、由岩石和大理石做成的各式各样的十字架、奇形怪状的栅栏。墓与墓之间长着高大的树,只要能生长草木的地方都长了灌木丛和野草,到处落满了黄色的树叶。这儿葬着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陆军统帅、海军将领、社会活动家,最后是一般有钱的人。
特里橱诺夫沿着踩出来的小路走到了转弯处。访问药房的女人就在这里转弯的,并且不知隐藏到哪儿去了。真的,在这些丛林中甩掉个跟踪的人不难办到,只需往旁边走上两、三步。特里福诺夫沿小路往前走了一会,转了个弯,藏进了一簇丛林里,环顾了一下四周。在他身后铁栅栏的后面,竖立着个由黑色磨光石做成的,落满了黄叶的高大十字架:右边和左边有两棵树,透过落了树叶的丛林,可以清楚地望到转弯处的一段小路。
时间还有,可以抽支烟。
过了几分钟传来了女人的笑声,小路上出现了一群穿棉衣的妇女。前面走着个高高的姑娘,用细枝条打着还连在树枝上的枯叶,后面走着三个人。
“啊呀,姑娘们,看!”其中一个拦住了朋友说,“像是个人……”刹那间特里福诺夫僵住了,以为姑娘发现了他:但即刻就放心了。姑娘们看着的是上面某个地方。
“这不过是个错觉。是小教堂上什么东西坍毁了。”
“多么像呀!对吗?看……有一双手,有头,还有帽子……跟人像极了……牙齿里还咬着线。”
“别瞎想,纽尔卡!”
“不,真的,看!”
“那是树枝。”
“又细又直!跟线一模一样。”
“姑娘们!你们在那儿干什么呀?”前面的人等得不耐烦在喊。
“马上走!纽拉在这儿看见了个人……”大伙儿往前走去,到了转弯处,又停下了。
“喂,你的人呢?”“是……现在不很像了,不过那根线我还能看到。”
“那不是线,是根什么导线吧。”
“走吧,走吧!”很快声音静下来了。瓦西里·阿列克谢那维奇点燃了熄灭的烟。
“为什么在墓地上人们特别敏感,会有各种鬼怪的幻觉?”他想,“无缘无故地在小教堂的什么地方看到了一个牙齿里咬着线的人。”
又传来了脚步声,小路上出现了两个中年人。他们慢慢地走着,低声谈论着。
“我下限你争……辩论家,可能是个小城市,但主要的是罗科索夫斯基打下的,这儿还有给瓦杜丁的命令。科罗斯腾拿下了,”第一个兴奋地说,”德国人给打垮了,已沙。”
“在斯大林格勒他们就被打垮了,库兹米奇,”第二个用深厚的男低音说,”在那里德国人的土气就开始低落了,我们现在情绪空前高涨。这一向如此……俄罗斯人发动起来难,可一旦发动起来,就谁也别想拦得住……”
关于占领科罗斯腾和罗科索夫斯基军队的进攻,特里福诺夫还在昨天就知道了。”可见命令已由无线电广播了,”他想。
不知不觉临近了黄昏。灿烂的、磨光的大理石的表面暗淡下去了:轮廓分明的十字架墓碑开始失去了自己的形状,并且与植物的景色溶成一片:残叶从树上脱落下来,掉到地面,现在它们更像是一种奇怪的蝴蝶在飞舞。湿气钻到身体里,一分钟比一分钟冷起来。
“可见弄错了,”特里福诺夫烦恼地想,“又放过了第二个,真是不走运。”
“他已经准备离开隐蔽的地方了;正在这时他畸见了沙沙的声音,有谁在小路上走来。特里福诺夫伸长了头颈,屏息凝神。有人走近了转弯处。
“是他!”尽管天有点暗了,特里福诺夫还是立刻认出了药房的访问者。芬兰帽、眼镜、“小萤火虫”。男人走得很快,走到转弯处立停了,四面环顾一下,看见没有人,就沿着小路大步走去,在一个耸立着白色大理石十字架的铁栅栏附近转了个弯。特里福诺夫往前移动了几步。男人的黑影在小教堂的背景上闪了一下,接着又在一簇矮灌木丛后出现了一次,就不见了。
他一时真想冲向前去,躲在丛林后,走斜角跟踪那个人,但不知什么力量使他没有这样做。
“不能这么干!人家会发觉我的。”特里福诺夫觉得自己呼吸都很困难,心怦怦跳得厉害。大概他好久忍住了呼吸,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原是这么回事,”他深深地呼吸了口气想,”就算这次又放过了他,但是方向总是找对了。现在可以得出个结论:在这墓地的什么地方……他们藏着什么东西,再不这就是他们隐藏的地方,”侦察员静静地细听各处传来的声音,心里一直在沉思着。
右边仓库后面,施利谢尔堡公路上偶而有驶过的汽车声:身后很远的地方响着机车的嘶鸣。但是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有生气的、熟悉的,跟“坟地的寂静”毫无关系。墓地上有着一种特殊的宁静,不管落叶的簌簌声,还是摆动树枝的飒讽风声,没有打破这一宁静,反倒使它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