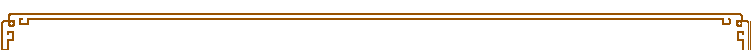电话铃响时,厂长办公室正在开会。坐在附近的总工程师取下了话筒,用手掌半掩着传声器,低声说:“喂,请等会儿来电话。现在他正忙着……怎么回事?您说什么!真是出乎意外……好,我转告他。”
挂好活筒,总工程师俯向厂长,用耳语转告了来话的内容。这时在发言的工段长停止了说话,以便让厂长注意听总工程师的话。房间里开始一片肃静。根据总工程师脸部的表情,大家都感到发生了某件重大的事。厂长的双眉锁了起来。
“同志们,”他说着不知为什么举起了一只手,“我应当告诉你们一个沉痛的消息。科茹赫牺牲了……”
“是父亲吗?”一个战前与瓦夏的父亲一起工作的工长打断说。
“不。是儿子。瓦夏·科茹赫。”
“不是大家都在说,他不要紧了……健康正在恢复。”
“是的。可在昨天的炮击中,他牺牲了……”
“把人毁了,畜生……”
又开始一片寂静。所有在场的都认识现在前线作战的科茹赫,认识他的妻子,也认识在厂实验室里工作的瓦夏。男孩子的英勇行为使车间免于火灾,为此受了严重烧伤,这使大家更加喜欢瓦夏。他在一年的工作中早就表现出是个当之无愧的接班人和真正的爱国者。
“请等一等,”厂长说着拿起了内线电话,“给我拴共青团委员会。你是谁?是这么一回事,瑟乔夫……军医院刚通知我,瓦夏·科茹赫牺牲了……不,死了……嗯,当然是完全死了……你等等。听我说,现在去一些小伙子,把尸体运回厂里……对。举行一个共青团式的葬礼……什么?你们什么地方较方便?不,实验室不行。最好在你们的委员会里……给组织一下,”
讲完话,厂长把脸转向了工会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你来负责……要通知他母亲。让她有个准备。”
“哎哟……同志们,我不会,”工会主席把手放到胸前带着哭腔说,“女人的眼泪我受不了……”
“这儿不需要特别的本事。没什么,没什么……她是列宁格勒人。”
“你,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更习惯于告诉别人们发奖金,”党委书记低沉地说,站了起来,“我去告诉他母亲吧。”
斯乔帕与萨什卡这两天都去了大修道院,并认真地捕着鸟。抓到了两只山雀,不知打哪儿来的权为什么飞来墓地的一只麻雀也落到了网里:但斯乔帕从早到晚挨冻,急需查明的事还是没有眉目。戴眼镜和芬兰帽的那个人再也没有出现过。
晚上,斯乔帕回到家里,碰上了不知为什么正在生气的母亲。
“你死到哪里去了!”她责骂儿子说,“整天你在什么地方?”
“咳,妈妈,你叫嚷什么?我出去是有事。”
“连知道都不想知道……别扯谎!你啥事也没有。应该去上班,而你不知在什么地方闲逛。”
“我这是受工厂的委托……”
“啊呀,老天爷,老天爷!炮击接着炮击,而他却满不在乎。你会像科茹赫一样落到炮弹底下去的。”
“瓦夏是在工厂里受伤的,在工作时,”斯乔帕反驳说,“没有什么,他很快就要恢复健康了。”
“恢复健康,你等着吧!不知在哪儿奔来奔去,追鸡撵狗,连明天安葬他也不知道。”
“你说什么话……安葬谁?”
“瓦夏。”
“你怎么啦!”
“还不相信别人的话。我对你说的是正经话。炮击时,瓦夏在军医院里给打死了。今天安放在共青团委员会里。明天下葬。”
三分未钟斯乔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继续说着她今天怎样去看望了纳塔利虹,纳塔利姚怎样坐在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像在等他睁开眼睛来看她,她很平静,并没流着眼泪回答她……
然而这些斯乔帕都没有听见。他的意识像给分成了两截。在他的头脑里。与脉搏一起跳动着这样两句话:“瓦夏死了。瓦夏没有了。”
可是他对这些话不能理解。在记忆的某个深处总存在个活泼、愉快而又坚毅的瓦西卡,不管这可怕的思想如何在敲打,却未能潜入他的另一个意识。
“瓦西卡怎会就此没有了呢?他能躲到哪儿去了呢?是的,我看见他绑着绷带躺在医院里。那又怎样?恢复了健康,就会起床的。他的脚一点也没受伤……战争结束,我们将一起开始学习。要知道这是我们早就说定的啊……”
“瓦西卡死了,瓦西卡没有了,”一个可怕的思想固执地敲打着。“那又怎样?现在死了,随后又将活过来,”斯乔帕的整个身心在抗议,并无论怎样也不能想象瓦西卡从生活中永远消逝了。
“妈妈,我去……”他费劲地说。
“你去哪里?”“我去……米沙那儿要去一次,”他说,虽然他完全知道,阿列克谢耶夫不在家过夜。
“先吃点吧,会饿着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芙娜表示反对,但看到儿子无心吃东西,也就没有坚持。
斯乔帕走到了院子里,不由自主地望了望科茹赫家黑洞洞的窗子,回忆起瓦西卡的请求——为了保暖给窗子加上胶合板,糊上报纸。他没有完成朋友最后的请求。“最后”这个词多么怕人!
“就是说,瓦西卡永远不再请求什么了……就是说,他再也不需要什么了。这是他的最后的请求。”
突然间斯乔帕明白,在他生活中发生了他以前从没想到过的事。在他的简短的一生中,他看到过许多死人。42年冬天,人们大批大批死亡。死人横卧街头,把他们堆成了堆,用载重车装走。从前线也传来各种各样人死亡的消息,但所有这些不知为什么未触动他的心。
只有现在,当生活中离去了如此熟悉,如此亲密,他如此需要的人时,斯乔帕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是死亡。
有一团什么东西塞住了他的喉咙,堵住了呼吸。胸口有个什么东西在发颤。他跑到了第二个院子里,躲在一只混凝上的污水箱后面号陶大哭,痛苦地哽咽着,不觉得脸红,也不掩饰眼泪,他哭了很久。随同痛苦一起,胸中不由自主说出了这样的话:
“哼……可恶的恶棍!”远处的一个港口开始响起了高射炮的撞击声。两辆汽车发出呼哧呼哧和啪啪作响的声音,喧闹地驶过大街。
“油箱里的汽油灌多了,”斯乔帕无意识地思索一下,不知为什么又回想起他们有一次乘“香肠”有轨电车去中央文化休息公回,瓦西卡用左手抓住他的衣领,为使他在转弯时不致跌倒。
第二天早晨斯乔帕起得很早。
“什么!又是委托?”母亲怀疑地问。
“不。我去找米沙,而随后去瓦夏的厂里。你自己说,今天下葬。”
“瞧,我……我忍了又忍,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到时候有你好看的。”
“行了……干吗你一大早就开始!”匆匆地吃了早饭,斯乔帕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到萨什卡那里去。东方的天空一片桔红色。天气仍然晴朗而寒冷。“又要炮击了,恶棍,”斯乔帕想了一下。就像回答他一样,又传来了大炮砰砰的声音,不久远处又传来了爆炸声。
萨什卡已准备好去墓地了。捕获的那些鸟激起了他打猎的狂热,不管瓦夏的死亡和安葬,他决定不取消外出,何况昨天傍晚又飞来了一群山雀。让斯乔帕去厂里给朋友送葬吧。这是他的责任和义务,他本人与瓦夏又不特别相好,因此还是去捕鸟。
“可能他就葬在那儿……尼古拉墓地上?”他问斯乔帕。
“不……这个墓地是关闭的。那儿要有特别的批准,只埋葬一些著名的人,”斯乔帕回答,“好吧,去捕鸟吧……如果有谁问起我,那你说……我……
你随便想个借口。”
“谁会问起你呢?”萨什卡感兴趣地说。
“嗯,不一定会。我有一个熟人。他可能顺便来看看。”
“那对他说什么?”萨什卡问,“去大小便了吗?”
“不。这不适合。你最好说,我生病了……或者不。最好说真话。有什么可撤谎的呢?最好我给他打个电话,不过时间太早。还有什么,萨什卡……要是那个人出来干涉……记得那个戴眼镜的假看守吗……你叫他走开点。明白了吗?别怕。他没有任何权利来管。”
“你怎么知道他有权利没有权利?”
“当然知道。你别怀疑……好吧,祝你满载而归……我尽量快回来。埋好瓦夏,立刻去你那儿。我还想出了个主意……最好在那儿偷一个墓碑,树在瓦夏的墓上。这样的墓碑在尼古拉墓地多得很……找一个漂亮的大理石墓碑……”
“它们都有十字架。给共青团员树个有十字架的墓碑那怎么行!”萨什卡反对说。
“这没有什么。十字架可以用凿子凿掉。”
“你可知道,它们有多重?”
“我们不用自己来抬。用载重车。”
“什么地方去找载重车?”
“这不用你操心。”一切商量定,朋友俩分手了。斯乔帕出发去找米沙·阿列克谢耶夫,而萨什卡则出发去捕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