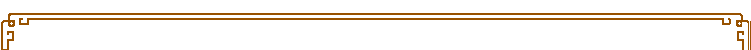我17岁中学毕业。这时就需要认真作出决定:将来干什么呢?
我下了决心:当一名飞机设计师。
可是,这要从哪里下手呢?去找谁呢?我连一个航空界工作人员也不认识。
我在报上常常读到工程设计师波罗霍夫希科夫的名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找他,但我还是决意去见他,请他帮忙把我安排在航空部门工作。
就这样,1923年夏天,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波罗霍夫希科夫。红军空军总局位于通往列宁格勒的公路旁边,我在总局大楼的前边一等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我窘迫羞怯地走到他跟前。波罗霍夫希科夫身材高大,体格匀称,穿着军装,佩带菱形领章。我想他是位很忙的人,所以简短地说明了我的请求,而我要跟他说的话却多着哩!
“跟我走吧,我们边走边谈。”波罗霍夫希科夫提议说。
我欣然表示同意。有多少次我从机场板墙缝隙向里面张望,我多么想到机场啊!
一路上,不知为什么,话总是谈不起来,我怎么也想不出个开头的话题。而设计师呢,看样子正沉浸在自己的构思之中。
当我们来到中央机场时,哨兵向我厉声问道:“到哪儿去?”
“跟我来的,”波罗霍大希科夫对哨兵说。
哨兵行个举手礼,我便走进了这朝思暮想的大门。
几乎没有机库,飞机就径直停放在露天场地上。
飞机场上,有几架是内战年代从外国干涉军手中虏获的飞机,若是现在看见这些飞机,也许会给人一种简陋得可怜的印象,可是当时,这些飞机却引起我由衷的喜悦。
波罗霍夫希科夫来机场是为了检查不久前才到来的一架法国“高德隆”式新飞机。我记得那架飞机的机翼和尾翼蒙皮平整光滑,是经过抛光的,有象牙般的颜色。但是就其整体来说,塞满了大量导管和导线,显得有点笨拙。
波罗霍夫希科夫检查了“高德隆”之后,又向另一架飞机走去。
这时我决定向他提提自己。于是,我同他一面走,一面开始说道:“我从幼年就渴望当工程师……”
我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完,我们已走到另一架陈旧的法国“莫朗”式单翼机跟前,波罗霍夫希科夫已开始与飞行员谈话了。过十来分钟,我们又继续往前走。
“我在航空模型小组工作,”我又开始说, “我对这个事业很感兴趣。我想当航空工程师,想当设计师,我请求您……”
可是,这时我们又走到了一架某种飞机跟前,波罗霍夫希科夫又开始检查这架飞机,边检查边向机械员提出注意事项。
我抓住时机,继续说道:“我现在就想进航空学校,或者您也许可以帮助我,把我安排到航空支队去当机械员……”
波罗霍夫希科夫心不在焉地听着,继续从一架飞机走向另一架,他终于办完了自己的事,连瞧也不瞧我一眼地说道:“现在很多人想当设计师,这不是严肃的态度。当设计师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不应该从这点起步。”
虽然我也知道,波罗霍夫希科夫没有工夫帮我张罗,可是我还是感到很难过。
然而做一名未来的设计师究竟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起步,波罗霍夫希科夫并没有说,他打发我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
我没办法,只好去了。
这个人听我讲完我的请求以后,就说道:“明天来吧。”
到第二天,他又说道:“明天来吧。”
下次干脆不接见我了。我明白在这里是达不到任何目的的。我不愿意再去找波罗霍夫希科夫,于是便开始寻找进入航空界的其他途径。
还在1923年初,报上就登出通告说,11月间将在克里木举行首次滑翔机竞赛。这时,我对滑翔机已有所了解,愿意参加制造苏联的头一批滑翔机。我决定去见竞赛的组织者,当时著名的飞行员兼设计师阿尔采乌洛夫。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阿尔采乌洛夫接见我时,非常亲切,深表同情地听完我的话,就马上提议说:“我介绍您去给飞行员安诺申科当助手,您愿意吗?他现时正在制造自己设计的滑翔机。”
“好,我当然愿意!”我高兴地回答。
制造滑翔机的人们在空军学院的大楼里工作。我还清楚记得,在彼得罗夫宫寒冷又没有生火的大厅里,堆满滑翔机零件和结构材料。我是个新手,看着那些制造滑翔机的人,我简直把他们看成是魔术家了。
阿尔采乌洛夫把我带到一位令人喜欢、体材匀称的人的面前说:“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你瞧,给你找了个助手,来认识认识吧!”
安诺申科向我伸出手来,说道:“您好!很高兴,您叫什么名字? 舒拉? 好吧,舒拉,工作吧……您会干得好的。”
“您将去克里木参加竞赛,”他补充说道。
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不过我以极大的热情动手制造起滑翔机来。
我在童年时代就学会了使用木工工具,因此我的工作干得不坏。起初,造滑翔机的许多活都是安诺申科亲自动手干,但他除了造滑翔机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事要他操心:他是滑翔机竞赛的组织者之一,因此当他确信我的工作干得挺顺手时,他就不再常来,即便来了,也只看看,指导一下。
当然,这样的信任使我不胜欣慰,我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制造滑翔机的工作使我深深着了迷,我整天都呆在学院的大厅里工作,父亲生我的气了,他希望我赶快找个好工作,他认为制造滑翔机是毫无用处的。
母亲相反,她袒护我,对父亲说:“让他干吧,这并不是什么一般毫无用处的怪念头,也许将来他真会成为航空工程师。”
我热切期望实现这个理想,希望总有一天会成为事实。
滑翔机竞赛的日期快到了,而滑翔机还没有造好,还要更多更顽强地工作。
这时,我得知,因为我积极工作,已决定派我去克里木参加竞赛,我高兴极了。我和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安诺申科答应到现场把我们的滑翔机的制造工作做完。
滑翔机竞赛地点选在科克捷别利地区——这是疗养村,在克里木半岛的东南部,靠近费奥多西亚。这个角落,后来成为全苏滑翔机运动员传统的集训地。
决定派一挂专用列车把参加竞赛的人员连同滑翔机一起送往克里木去参加竞赛。这挂列车有几辆敞车和一辆有取暖设备的客车。滑翔机装在敞车上,上边用苫布盖着,滑翔机运动员都坐在客车里。克里木之行是我一生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次。在这以前,我从未到过克里木半岛。我除了跟母亲出过门以外,一个人哪儿也没去过。这第一次独立的旅行,我觉得真是惬意极了!
我的衣袋里装着官方的出差证和旅费。
我在有取暖设备的客车里感到如登天堂。聚集在这里的都是些年轻人,都是航空爱好者,其中有滑翔机设计师伊留申、佩什诺夫和戈罗申科。这些人现在都是全国知名的人物。伊留申成了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佩什诺夫和戈罗申科成了科学家和教授,而那时他们都是空军学院的学员,已经在航空事业中迈出了开头的几步。
途中空闲时间很多。列车走得很慢,我们坐车一共走了六天。旅途时间虽长,并不使人感到厌倦。
在这几天里,我听到有关航空和技术领域很多有趣的谈话。我同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和善良的同志们交上了朋友,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从事航空事业的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我们从莫斯科出发的时候已是深秋,天气寒冷,雨雪交加。不过越往南走越暖和。到后来取暖客车里又热又闷,我们只得搬到敞车上去,睡到滑翔机旁边。白天,我们聚在一起谈天,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夜里,我们回到各自的滑翔机跟前,钻到苫布下,酣睡起来。
有一天夜里,一种不寻常的、莫名其妙的喧嚣声把我惊醒。我赶快起来,爬出苫布,向周围看了看……我望见了大海。这是我头一次看见大海,并且已近在身边,只有几步之遥。
列车停了下来。天空月儿又圆又亮,月光下的大海宛如泛着银光的巨大地毯,可以望见很远的地方,直到天际。
原来,我们已经到达费奥多西亚了。火车站就在海岸边上。我一直到早晨都在观赏着大海,倾听着海浪拍岸的喧声。
第二天,从专用列车上卸下滑翔机,把它们运到科克捷别利。在那里的山上布置了野营,支起了帐篷。
所有的滑翔机都已经在莫斯科造好,到这里只须组装起来,就可以马上放飞。只有安诺申科的滑翔机尚未完成,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安诺申科对我说道:“您在这里好好工作吧,我需要到现场去一下,我是技术委员会委员,不到起飞线不行。”
他的确应该到起飞线去,可是把我一个人留在离竞赛场地很远的地方,我的心情该是怎样的啊!
竞赛已经开始,滑翔机在飞翔,而我仍坐在帐篷里干活。
帐篷在离起飞线两公里远的地方,而我想看飞行并且想得要命。最后,我忍耐不住,扔下工作,跑去看竞赛了。
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在场上发现了我,他说道:“回去工作去吧,以后您都能看得见的。”
我没有办法,只好回去。不过我还是难以独自蹲在帐篷里工作。
第二天,我又跑到现场,这次竭力设法不让我的“主人”看见,我称心如意地观看了滑翔机的飞行。
现今苏联很多滑翔机都能飞行几百公里,创造高度纪录,完成精彩的编队飞行,做非常优美的高级特技。而那时,参加最初几次竞赛的滑翔机一共只有10架,而且谁也不知道它们将飞得如何。每个设计师内心深处只有一个愿望:但愿他的滑翔机能飞。飞得怎样,飞到哪里——这些都没有考虑,只要它飞起来,并能平安落下来就行了!
因此,当飞行员阿尔采乌洛夫设计的滑翔机从起飞线平稳地飞起来,然后飞了几小圈。顺利落到地上的时候,参加竞赛的人们欣喜若狂,向阿尔采乌洛夫热烈欢呼,跑上前去把他抬起来向上抛。
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的滑翔机也造好了。设计师不知为什么给它起个名字叫“蛮猴”。竞赛时看到别人的滑翔机之后,老实说,我觉得我们的“蛮猴”希望不大。
其他听有的滑翔机造得都象飞机一样,有操纵机构、机翼、尾翼和机身。唯独我们的“蛮猴”极其简陋,只有机翼和尾翼,没有座舱、操纵机构和起落架。起飞要飞行员自己架着滑翔机跑,用自己的身体保持机身的平衡才能在空中飞翔。
这架滑翔机的型式使我想起十九世纪末著名的德国滑翔科学家李林达尔制造的那架滑翔机。
许多人都对我们的滑翔机能否飞起来表示怀疑,所以所有参加竞赛的人都聚集到起飞线,急不可耐地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这位勇敢的设计师亲自担任了“蛮猴”的试飞。
这架滑翔机比我们预想的略重一些,并且重心没有安排好—机尾过重。当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安诺申科把自己的苦心创作出来的作品驾在自己身上,并把手伸进扶手里面的时候,而机尾竟重得使滑翔机不能起飞。于是便派我在滑翔机滑跑的时候在后面托着机尾,这样一来,我也就成了第一次飞行的“参加者”。
安诺申科为慎重起见,决定先在一个小山岗上试验“蛮猴”,而不是象其他滑翔机那样在山的斜坡上起飞。他选好位置之后,等待适宜的阵风,开始准备起跑助飞。
我洋洋得意地托着滑翔机机尾。突然一声号令:“一、二、三,开始!”
安诺申科也喊了一声:“起跑!”
我托着机尾,用尽全身力气跑起来。然而安诺申科是个又高又壮的汉子,我又小又瘦,他跨一步,我要跑三步,我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他。我托机尾实在吃力极了,安诺申科终于喊道:“松手!”
我松手放开机尾,滑翔机刚升起二三米,就在空中翻转过来……摔到地上了。
大家都朝摔坏的滑翔机跑过去。我们担心安诺申科的性命,然而他却安然无恙地爬出来了。
修复“蛮猴”已不可能,现在我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放心地观看飞行了。
飞翔着的滑翔机非常好看,它象一支白色的巨鸟,展开不动的翅膀,毫无声息地在高空盘旋。
对那些看惯了利用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声的发动机使飞机飞行的人来说,驾驶滑翔机飞翔似乎是难以置信的。这种不是借助任何机械式发动机,而是仅仅靠滑翔机的完善和飞行员的技巧的飞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航空这个职业。从这时起,我已完全成为航空界的一员了。
在科克捷别利参加滑翔竞赛时,我就有了亲自尝试设计一架真正的滑翔机的念头。我做过模型飞机,见过各种滑翔机的结构,但我没有受过技术教育,所以我觉得我一个人担负不起这么困难的任务。
需要找人请教请教。我决定去找空军学院的学员谢尔盖·弗拉基米罗维奇·伊留申。我发觉从参加滑翔机竞赛时起,他就一直对我很好。
伊留申对我的打算表示赞同,但他提醒我说:“在这方面仅有愿望是不够的,还要有知识,才能正确设计滑翔机。当然许多事我可以替你做,如计算和画图,不过这样做对你好处不大。如果你独立地干,我可以帮助你,给你出主意,不懂的地方讲给你听。”
伊留申把他的飞机结构和强度计算课笔记给我阅读,并为我指定了一些必读的书籍。我如饥似渴地研究了这些笔记和书籍,然后我才着手研制滑翔机,遇到某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找伊留申。
那时,伊留申的妻子和小女儿同他一起住在空军学院的宿舍,在费尔曼内伊胡同一个不大的比较狭窄的房间里。每当晚上我去找他的时候,他们都是先把小女儿伊拉安排睡觉,我对此很不好意思,我给他们添了麻烦。但他们待我总是那么关心,和蔼可亲。伊留申在空军学院学习,他的时间很少,而他却情愿帮助我。我们有时一连谈上好几个小时,常常坐到深夜。
这是我的第一所技术学校。
当我在伊留申的帮助下,作完滑翔机的全部计算并绘完全部图纸的时候,在我面前就出现了在哪里和同谁一道制造这架滑翔机的问题。这时,我想起我不久前毕业出来的母校,于是,拿定主意,到那里组织滑翔机小组来制造滑翔机。
我来到了母校,首先同古沙淡起制造滑翔机的事情。
这个瘦瘦的、腼腆的、姓这样一个可笑的姓的小伙子是一位性格非常坚强、热爱劳动的人。
我对他说明我的来意。古沙认真地听完我的话,然后郑重其事地问道:“我们是制造真正的滑翔机,还是胡闹呢?”
“当然是真正的。”
这时我记起安诺申科过去曾对我做过的许诺,于是补充说道:“好好干,你也会去克里木参加竞赛的。”
古沙怀疑地微微冷笑道:“你算了吧,竟说大话!”
虽然他不相信会去参加竞赛,还是非常热心地干起来。他和我的另一位同学萨沙·格里申都成了制造滑翔机的热心人。
有十五个学生参加滑翔机小组,制造工作热烈展开了。同学们下课以后,就聚集到一起——有的人刨,有的人粘胶,有的人锯,有的人钉钉。
材料是从航空工厂弄来的,凡是滑翔机用的所有零件,乃至最为细小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造的。
我们在学校的体育厅里制造滑翔机,其他同学们经常到这里来观看。有些人讥笑我们是异想天开,不相信我们会做出点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然而大多数学生是同情我们的,尤其当清楚看到正在造出一个某种机器形状的时候。固然,一开头这还只是远未成形的构架——一些木条、木板和钢丝的堆叠而已。
滑翔机需要绷蒙布,我们这可遇到了大困难:一切都造好了,似乎什么都办到了,然而却不能绷蒙布,小组的男孩子不会做缝纫活。
“只好叫女孩子们来,”古沙说。
女孩子们很乐意来帮忙,她们用灵巧的双手很快就给滑翔机绷好精制的蒙布。
在学校上课期间,每天晚上我们都工作得很好而且很愉快。可是暑假一到,我们的小组就开始减员了:伙伴们有的去夏令营,有的去乡下,有的去避暑地。到工程快结束的时候,一共只剩下五个人。不过这五个人都是最热诚的航空爱好者。我们都很希望在竞赛前把滑翔机造好,可是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需要干几个通宵才行。
终于,一切准备就绪。专门委员前来检查,作出肯定的结论——允许我们的滑翔机参加竞赛。
现在,该我关心我的助手们了,他们得到了去克里木的权利。于是,我给古沙和格里申取来参加即将在科克捷别利举行的全苏第二届滑翔机竞赛的出差证书。我理解他们这时的自豪心情,因为仅在一年前我自己也曾有过同样的经历。
我们把我们的宝贝装上敞车,小心地给它盖上苫布,这挂运载滑翔机运动员的专用列车便向克里木进发了。
在乌仲—赛尔特山上,许多航空帐篷中有一间停放着滑翔机,其中有别人的,也有我们的,都是在两天内组装起来的。
滑翔机的蒙皮浸过硝基清漆,因此帐篷里散发出象指甲修整室里的那种刺鼻香味,每个闻过这种味道的人都会终生难忘。
第一天,天气晴朗,有点小风,大家就把滑翔机牵引到起飞线。经过技术委员会彻底检查之后,驾驶员坐到座舱里,用皮带把自己系在座椅上,挂上橡皮绳。这时,起飞信号员就位。
“注意!”起飞信号员举起小旗,一起阵风,他就把手一挥。滑翔机滑跑起来,然后抬起机尾,很快就离开地面,爬升到不很高的空中。我、古沙和格里申看见我们的创作飞上了天,感到非常幸福。这时,我们紧张得心脏象要停止跳动似地,眼盯着滑翔机静悄悄地向山脚方向滑翔而去。
驾驶员很满意。这架滑翔机在空中既稳定,又很听舵的操纵。此后,几乎每天都飞它。人们公认,这架滑翔机的结构是成功的。我得到了二百卢布的奖金和一张奖状。这次成功鼓舞了我。
制造滑翔机的工作对古沙并非毫无影响,他也从此终生成了航空界的一员。几年后,我遇见过他,那时他已是军事飞行员了。
一年以后,我又设计了一架新的滑翔机。
在科克捷别利获得成功之后,我比以前更加向往受到航空教育,可是未能进入当时我国唯一的航空最高学府——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
进入这所学院,要求在红军服役的年限。我不具备这个条件,因此我决定从航空兵基层开始进入空军工作,到飞机修理工厂当工人。
有些同学不赞成我的这个选择,他们对我说:“进不了空军学院,就考别的学校,主要的问题是不要耽误时间,不然以后无法弥补……”
然而我绝不能改变我的爱好,背弃我热爱的航空事业。我不能设想去当医生,或者譬如说去当教员。
可是,一个中学毕业生毕业后马上进飞机修理厂,看来是不可能的。这时我去到拉赫曼诺夫斯基巷现在卫生部所在地的那座大楼,当时是职业介绍所。我登记失业,请求分配我去任何工厂。但是我的计划——一有可能就转到空军工作——并未放弃。
那个时期,很难找到固定的工作。内战后,国家刚开始恢复不久,老工厂已经开工,而新工厂尚未建立起来。职业介绍所挤满了失业的青年。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和其他跟我一样的年轻人一道,拿着职业介绍所的介绍信去干从货车上卸下木柴、砖或土豆的工作。
记得头一次是派我去卸土豆。那天很冷又刮着风。在离车站很远、通往雅罗斯拉夫的铁路干线的卸货线上,停着一列等待卸货的军用列车。起初,我们不知道从何着手,工作进行得不太顺利。干这种活应该先把车皮推到卸货台,再把货物卸到带盖的堆栈里。不过,后来我们总算会干了。大家很快就混熟了。工作吸引住我们,青春的活力发挥了作用。唱歌,说笑话,这些对工作很有帮助。休息时,我们就在露天吃那些烫嘴的、带皮的烤土豆,这是多么快活啊! 滋味有多美啊!
工作结束时天已黑了。我没干惯重体力活,所以感到非常疲倦,不过情绪却很好。不仅我是如此,所有和我一同工作的人也都感到很满意。
后来,我又被派去干了几次各种临时工。到1924年3月,在伊留申的帮助下,我终于进了空军学院的教学工厂。
我被分配到木工车间。一开头,车间的工人们用一种怀疑的目光斜着眼看我。的确,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有中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人,竟然来侍弄圆锯和大刨子,每天从早到晚都背着胶合板箱,把锯末和松木刨花装运出去。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这种怀疑的心情是自然的,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中等教育还不普及,几乎每个中学生一毕业都设法进入大学。
我的工作很多,刚运走满满一箱子,车床旁边又堆起一大堆锯末和刨花。这样的工作通常是由刚从农村来的技术最不熟练的工人来做的。
一开头,他们对我的称呼不用“你”和“同志”,而用“您”和口气不那么确定的词“年轻人”。在工间休息的时候,总有来自各车间的五六个人到“吸烟室”围坐在木桶旁吸烟,周围笼罩着马合烟冒出的暗兰色烟云。特别当我从这里走过的时候,我猜想他们在背后指着我发些嘲笑的议论。但是这并未使我狼狈不堪。最后,大家终于看出,我并非是不爱劳动的人,我从不拒绝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无论交给我什么活,我总是一个劲儿勤勤恳恳地干。
人们经常看见我手里拿着扫帚或者是从仓库往机加车间搬运很重的钢锭。最初,我这双手很不熟练,又不太灵巧,擦伤了常常用抹布包缠起来。不过照我现在的看法,这对我也很有益处。
同事们对我的态度终于改变了,我也跟别人一样成为这个集体的一员。
我从未因做辅助工作——听工人们叫我“拿来”、“拿住”、“清除掉”等等而感到不好意思。我用心熟悉周围一切,耐心地学:逐渐学会了研磨刀具,往车床卡盘上固定零件,掌握了焊机的焊枪使用方法。两年中,我便知道了主要生产过程,学会自己动手制做很多东西。
当我在修理厂工作一年半到两年之后,才达到了调到机场飞行支队的目的,这时我已经懂得劳动是怎么回事了。
1925~1926年的莫斯科中央机场,外观与今天迥然不同。绿色的机场上,没有混凝土起飞着陆跑道,因为那时的飞机完全不需要这样的跑道。
机场边上,有几座木结构机库。 一座是我们飞行支队的,挨着我们的一座是属于德—俄航空公司的。其次的几座机库里面存放着“杜克斯”(从前是莫斯科自行车工厂)工厂生产的“埃尔—1”(P—1)型飞机,再其次是莫斯科军事飞行学校的机库。
机场的东边与几所军用仓库和“航空工作者”工厂搭界。我过去自己造滑翔机时曾经跟这个工厂要过零件和材料。机场的北边是通往列宁格勒的公路;西边是个大沟,摔坏的飞机都扔到这里,南边则是阵亡将士墓,是牺牲的飞行员安葬地。
由于飞机少,机场上不常飞行,只在天气好的时候才飞。德—俄航空公司的班机飞行员却是例外,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有希班诺夫和鲍勃科夫。这些飞行员驾驶“福克-3”旅客机飞莫斯科一哥尼斯堡航线,不管什么天气都按班机时刻表准时飞行,哪怕你对着表检查,分秒不差。
我乍去机场工作的时候,交给我的工作并不复杂:我担任“机库主人”的职务。我负责保持机库整洁和秩序,清早开门,夜晚关门,也就是要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的直接首长是支队主任工程师阿列克赛·阿尼西莫维奇·杰麦什凯维奇。他个子不高,胖胖的,心地善良。人们当面和背后都叫他“老爹”或“老大哥”。他见我非常努力履行我的职责,并且对飞机十分感兴趣,不久便调我去当二级机械兵。
这样,我就达到了目的:从早到晚同我的上司、一级机械兵沃洛佳·科罗利科在我们的“安萨利多”飞机的周围奔忙着。
我们飞行支队有三种类型飞机:一种是国产的双翼机“埃尔—1”,有3~4架,另一种是意大利的双翼机“安萨利多”,也是3~4架,最后一种是几架列宁格勒“红色飞行员”工厂按缴获的英国飞机“阿弗娄”仿制的教练机,人们通常叫它“阿弗鲁什卡”。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把飞机从机库推到停机线,加满汽油,进行发动机地面试车,然后等待飞行员和学院学员的到来。大队长是尤利安·伊万诺维奇·皮昂特科夫斯基。后来命运把我们两人长期联结在一起。
支队长皮昂特科夫斯基,政委切尔尼亚耶夫和主任工程师杰麦什凯维奇是支队的灵魂,他们三个人都热爱航空,并且也用这种精神来教育自己的部下。皮昂特科夫斯基教政委学会飞行,这时切尔尼亚耶夫已开始单飞了。
尤利安·伊万诺维奇或尤利克——同志们这样称呼他,是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技术爱好者,心灵手巧。经常可以看见他卷起袖子在车间虎钳旁边干活,他的手艺不比任何钳工差。他自己的自行车,稍后奖给他的“哈莱”牌摩托车以及更晚一些时候的“嘎斯”牌汽车都弄得格外清洁,闪闪发亮,而且总要加装上自己发明的某种辅助装置,并做出某些改进。
我跟皮昂特科夫斯基去飞行的机会相当多,有一次他表演高级特技,几乎使我失去知觉。
起初,支队有些同事对我抱着有点讥笑的态度。他们从外表上看,以为我是家里娇生惯养的孩子,然而他们却没有料到我是那样勤奋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样乐于接受交给我的任何工作,从不计较时间,所以不久大家都把我当自己人看待了。
中学毕业三年之后,我们同班同学一齐来到约定的地点聚会,大家一起谈谈心,聊聊谁在做什么,工作安排得怎样。开始他们没有认出我,我这时已是一个晒得满面黝黑的红军战士,脚穿长筒皮靴,身着士兵大衣,头戴布琼尼式军帽,佩戴着浅蓝色的空军领章。
机场上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充满着浪漫情趣的,尽管要干的活多得不得了,当时没有任何机械设备,一切都得用手去做,也就是我们机场上说的那句老话“自食其力”。
“安萨利多”飞机安装的是360马力的“菲亚特”发动机。这种发动机很调皮,虽然我和沃洛佳·科罗利科两人为使它的工作良好,花的时间不计其数,它还是经常在着陆后自动停车,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熄火”。飞行员爬出座舱,疲惫地慢悠悠打道回府,那只好派红军战士来帮助我们了。
“安萨利多”的机尾很重,尾橇是汽车的板式弹簧,因此需要很多人。
“抬起机尾!”沃洛佳指挥,包括我一共四个人用肩扛机尾,八个人撑住机翼向前推动飞机。我们齐声喊:“推呀!”
就这样,机尾朝前,机头在后,我们要把飞机推到一公里远的距离,恐怕还要远些。夏天倒不要紧,可是到了冬天可就困难啦!
那时,机场不扫雪,飞机用雪橇板滑跑,而不象现在用机轮。机场上没有拖拉机,只得在没人踏过的雪地上拖曳飞机。从旁边看去,这幅景象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想起列宾画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那幅名画。
那时,起动发动机也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安萨利多”飞机。需要先把螺旋桨扳转几次,再从发动机注油活门注入汽油,然后开始起动。
我先用手扳住螺旋桨的桨尖,然后喊道:“打开电门!”
“是! 打开电门。”沃洛佳从飞机座舱里回答,同时打开电门,接通磁电机。
我猛扳桨叶,助手拉住我的另一只手。螺旋桨转了半圈。然后再重复“打开电门”,“是! 打开电门”这个程序。这样,我和助手手拉着手,就象童话中说的“老奶奶拉住老爷爷,老爷爷抓住大萝卜”那样,我们多次扳转螺旋桨,最后直到发动机发出粗声粗气的吼声,象打喷嚏似地喷出白烟为止。发动机起动之后,经过小转速加温,排气管后面便舞动着短而均匀的青蓝色火舌。
汽油装在大油桶里用运货马车运来,冬天则用运货雪橇。我们把汽油倒进提桶,然后登上梯子,经垫有麂皮的漏斗把油加进飞机油箱。油箱可装150~200公升汽油。加完油用手把装在小雪橇上的加水车(这是一个烧热水的小锅炉)拖到跟前,再用提桶往散热器里加水。滑油装在提桶里放在炉子上加温,将近沸腾时,提到停机线加到飞机的滑油箱里,这些工作不论刮风或严寒的天气都是在外场进行。
又譬如擦净被滑油弄脏的或结了冰的飞机机尾,究竟有什么必要! 你得倒半提桶汽油在里面把抹布涮涮,再去擦拭机尾。天气冷得很,手都冻麻木了,更确切些说,是冻僵了。由于汽油挥发,手全变成了白色,但这些活不能不干。因为只要所有的活还没干完,沃洛佳还未把电嘴都拧下来,而我用清洁的汽油还未把它们都洗干净,只要飞行员提出的故障尚未排除完毕,“老爹”是不会验收飞机的。
把飞机拖进机库也不那么容易。雪橇式起落架在混凝土地面上是不滑动的,因此只好先在地上撒上雪,这样才能把盖着蒙布、准备明天飞行的飞机推到原来的地点。
好不容易到了休息时间,走进“小暖箱”里呆一会儿该有多么快活呀!在这狭小的装运飞机的木箱里挤进10~15人,难闻的烟草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小铁炉烧得通红,然而这令人极为快乐的温暖、说笑话以及引起的笑声,我特别喜欢听的饱经世故的“老头们”讲的《猎人的故事》,使这个10~15分钟的休息不知不觉地过去。只好惋惜地告别吸烟室,又重新走到寒冷、刮着大风的场地上去。
那时,我在机场看见许多有趣的事,因为那正是我国空军的初创时期。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波里卡尔波夫和图波列夫设计的国产飞机上了天,我是这些有历史意义的飞行的见证人。
机场上那座不大的两层塔台至今还完整无损,从前这座楼的尖顶上飘摆着被风吹得鼓鼓的、红白两色分明的麻布“香肠”(即风向标—一译者注),给飞行员指示着陆方向。
中央机场场长的指挥所就在这座塔楼里,每逢新飞机试飞或是机场上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时刻,在塔台的阳台(指挥台)上就出现了一位个子不高、仪表端庄,身着军装的机场场站主任——济诺维.尼古拉耶维奇.拉伊维契尔,背地里我们都管他叫济诺奇卡。他只稍稍留心看一下他的管辖区,任何小事也躲不过他那敏锐的眼睛。
三十年代初,我和尤利安·皮昂特科夫斯基,夏季几乎每天下班后都在试验我们新设计的小型运动飞机。而每次飞行的时候,“船长台”(指塔台——译者注)上总是可以见到机场场站主任拉伊维契尔,他对我们的工作很感兴趣,并表示同情。
济诺维.尼古拉耶维奇后来在新飞机的设计和试飞工作中,对我和皮昂特科夫斯基帮助很大。他热爱航空事业,而且是个很好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