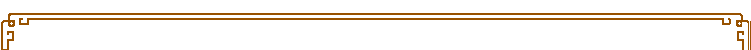1931年,我在空军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缅任斯基工厂。在这个厂里工作的有以设计师德米特里·巴甫洛维奇.格里戈罗维奇和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波里卡尔波夫为首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一批航空工程师。
这时,格里戈罗维奇,波里卡尔波夫,另外还有几位老专家因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判刑坐牢,不过,还让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在改成内部监狱的秘密的“第七机库”里生活和工作。
除这些人外,在这个工厂里工作的还有雇佣的设计师,他们由谢·亚·科切里金、阿·纳.拉法埃梁茨领导,后来由谢.弗.伊留申领导。
整个机构总称为中央设计局,它受设计总局技术处管辖,由处长戈里扬诺夫和厂长帕乌弗列尔直接领导。
这个设计局机构庞大,工作杂乱无章,开支很大,而成果却很少。只有波里卡尔波夫的工作是出色的,他在1930~1934年间研制出歼击机“伊-5”,“伊-15”,“伊-15比斯”和“伊—16”,而伊留申则在1936年研制出“中设-4”(UKB—4),即“伊尔—4”飞机。
应当指出,“伊—5”飞机开始飞行后不久,格里戈罗维奇以及其他在押的老专家都获释了。
当时,我国只有两个从事新飞机研制的规模大的设计中心: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中央设计局,另一个是由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领导的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设计局。他的最亲密的助手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汉格尔斯基、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彼得利亚科夫和伊万.伊万诺维奇·波戈斯基。
中央设计局研制轻型飞机,主要是歼击机、侦察机和强击机,而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设计局则侧重研制重型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和旅客机。
我带着航空工业总局的干部介绍信到缅任斯基工厂的干部科报到,而工厂干部科让我去找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科切里金面谈,他是一个设计小组的组长,我早就认识他。
科切里金过去当过海军军官,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知识分子,不时爱惜地抚摩着他那修得漂漂亮亮的棕黄色鬓须。他把我让到扶手椅上坐下,开始用工作远景引诱我去他的设计小组,他建议我研究飞行中收放起落架的问题。当时这是一项新的改革,我国的任何一架飞机上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科切里金早已非常清楚地知道我是一个设计师,所以竭力劝我到他的设计小组工作。
如果我同意他的建议,那就意味着我自己将陷入专业面狭窄的专家工作中去,而我向往的却是范围比较宽的设计活动,因此我毫不客气地断然谢绝了他,这使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失所望。
第二天,我向工厂厂长帕乌弗列尔说明我拒绝去科切里金那里工作的理由,并请求派我到生产第一线去当一名普通的工程师。到生产中去,我可以好好研究车间工作、车间计划和工艺规程,而这些知识对设计师是很宝贵的。
帕乌弗列尔立即表示赞同,于是,我就开始担任车间工艺师的工作。以后的实践证明我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样做,短时间内就可以达到每个设计师必须具备的那样的才智,即他应该知道如何在生产中——在机床上、工作台上、在装配架上——再现他在图纸和文件上所表达的思想。
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仍旧继续从事新的体育运动机和小马力轻型飞机的设计,每天在工厂干到深夜,所需经费由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拨给。工人们在业余时间照我的图纸制造新的飞机的零件,按后援会的规定付给特别工资。
缅任斯基工厂是一座大型企业。就这样,在二、三年的时间里,在工厂各个角落,不知不觉地一架接着一架造出了“阿伊尔—5”、“阿伊尔—6”和“阿伊尔—7”飞机。
“阿伊尔—5”飞机(人们都管它叫“空中福特”)是五座单翼机,汽车型座舱,装220马力的美国“莱特”发动机。大家都很喜欢这架飞机。后来我们甚至还给政府的一些成员作过表演。但是这种“莱特”发动机在苏联只有一台,是买来做样机的,因此,这架飞机没有前途。但它的型式很吸引人,我决定修改设计,把飞机有效载重减小,改装我国成批生产的100马力的发动机“埃姆—11”,这就是“阿伊尔—6”飞机,它的座舱可以坐三个人:飞行员和两名乘客。经过飞行试验之后,博得了普遍好评。这是我设计的投入批生产的第一种飞机,生产了大约1,000架左右。国民经济各部门用这种飞机作通讯机,在民航方面也得到了应用。
此外,按上述同样程序,又研制出“阿伊尔-7”飞机,动力装置采用的是本国批生产的“埃姆-22”发动机。
歼击机“伊-5”也使用这种发动机。“伊—5”是单座双翼歼击机,是格里戈罗维奇和波里卡尔波夫领导研制的,在当时来说是第一流的飞机,最大速度已提高到每小时280公里,并具有极好的机动性能。
起初,我认为“伊-5”在设计技巧上是高不可攀的典范。虽然我很喜欢它,但我对它进行仔细和长时间的观察之后断定,如果再大力改善空气动力性能,仍装这种480马力的“埃姆-22”发动机,是能够造出速度更大的飞机来的。
“伊—5”是双翼机,而双翼机比单翼机的迎面阻力大。单翼机用同样发动机可以得到更高的飞行性能。因此,我拿定主意要研制一种双座的、速度可望不低于每小时300公里的单翼机。不过,这是全新的任务。当时我国作战航空兵装备的全是双翼机。
我把装用同样发动机的单翼机和双翼机相当快地做了一番对比计算。我的假设得到了证实:单翼机不仅能够得到更快的速度,而且还可以做成双座飞机。
我担心自己的结论可能有误。又去找专家们商量。证实了我的计算并没有错。
画完飞机的设计草图,我在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的技术委员会上论证了装用“埃姆-22”发动机的双座单翼机每小时可以达到320公里的速度。
会上,有的人不同意,甚至敌视我的提议,然而大多数人表示赞同,于是便批准了这个设计方案。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拨给了研制费用。我成功地用研制完全新型的、在我国空军中速度最快的飞机的理想感染了我的最亲密的助手们。于是,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和工人们很快就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很小的、然而却很和睦的集体。
我们绘制出飞机图纸,然后就开始干起活来。老实说,工作是半手工式的,因为我们既没有供制造飞机用的场所,又没有设备,而制造我们的飞机对工厂来说又是计划外的,可以说是一种半合法的形式。不过,工厂各车间的同志都尽力帮助我们。
说真的,现在回想起当年我们生产飞机的那种条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们居然能在工作制度非常严格的工厂里完成那样的“地下”工作!
1932年夏末,当“阿伊尔-7”组装完成拖出车间并出现在机场上的时候,引起全厂上下从厂长到全体员工的强烈反应,他们惊讶得两手一摊地说:怎么这样快,而且连厂长都不知道就造出这样一架飞机?!
“阿伊尔-7”飞机的问世,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一方面是空军和工业部门的领导对它很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工厂和设计局的领导看出这架飞机是一个危险的竞争者。
如果“阿伊尔-7”不发生事故那该多好! 关于事故,那是后话,这里暂且不提。
飞机的试验飞行仍然由主任飞行员尤利安·伊万诺维奇·皮昂特科夫斯基进行。这位优秀的飞行员具有试飞员的一切品质。他勇敢而又谨慎,对待飞行总是非常镇静。
我与皮昂特科夫斯基商量好,如果他在首次飞行中发觉飞机哪怕有微小的故障或者看到飞机飞行得不正常,就立刻返场着陆,不要象通常那样在机场上空绕飞一圈。
为了不招引看热闹的人,我们决定星期日大清早就试飞。在约定的时间,机场上来的人为数不多,光是那些应当出席首次飞行的人。我紧紧地握了握皮昂特科夫斯基的手,然后退到一旁。
飞行员坐入前舱。后舱乘客位置上固定了80公斤的配重。
发动机起动了。皮昂特科夫斯基仔细地进行了发动机试车,他让飞机在地面稍微滑跑了一段,然后起飞,离地2~3米飞行了约一公里,又重新着陆,滑行到起飞线,问道:“一切正常,可以起飞吗?”
我肯定地一挥手,飞行员立即加大油门,发动机轰鸣起来。飞机往前冲去,很快便离开机场的绿色草坪腾空而起。我们屏住呼吸,注视着飞机。爬升到300来米高度以后,飞机掉过头来在机场上空绕圈飞行,一圈,两圈,三圈,四圈……飞行员绕飞的圈数越多,我的心里越感到轻松,这就是说,一切正常。
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们怀着幸福和满意的心情,向飞行员跑去。皮昂特科夫斯基从座舱里探出身来,打了一个手势表示:好极了!
当他爬出座舱的时候,大家一齐拥过去,把他抬起来,向上抛。每逢完成新飞机试飞,通常都要这样做,当然倘若一切顺利的话。
在这之后,我问尤利安:“请您实说,您认为这架飞机怎么样?”
“好极了! 我毫不怀疑它的速度每小时会超过300公里。”他回答说。
这使我非常高兴,我决定亲自参加飞行,检验一下飞行速度。
第二天,我和皮昂特科夫斯基一起飞上了天。我请他尽可能飞出飞机的最大速度。
尤利安爬升到所需高度,然后改成平飞,随即高声喊道:“喂,现在请注意!”
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空速表。只见仪表指针从180一190转到200,240,250,270,290,300……我继续盯着仪表,看它的指针停在什么地方。指针仍旧不断转动……310,320,330。指针终于停止转动。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和自豪。
我的飞机的飞行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30公里!这也就是说,一种速度最快的飞机研制成功了。
空速表的指针刚一停止转动,我就注意观察在当时从未有过的高速度下飞机各部件的状况究竟怎样。一切很正常:没有任何振动,也没有可疑的杂音和噪声。发动机发出强劲而均匀的响声。这说明,我们的计算和假设是完全正确的:单翼机与双翼机相比,优点特别显著。
正在这时,皮昂特科夫斯基向我转过脸来,我见他面带笑容,神采奕奕,我真想就在飞机里狂吻几下我的朋友。
我们安全着陆了。从飞机上下来,面向机场的场地,感到自己在速度竞赛中获得了冠军。
这架飞机头几次飞行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空军指挥机关想看看我们飞机的飞行。
来看的那一天,从早上起天气就不好,下着蒙蒙细雨。军人们到来之后,商议了好一会儿,看是否应该放飞。最后决定可以放飞。
皮昂特科夫斯基登机坐到驾驶员的座位上,试了试发动机。后座舱的乘客是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副主席列夫·巴甫洛维奇·马利诺夫斯基,他十分热爱航空事业,是个颇有魅力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飞机起飞滑跑不远,就轻飘飘地离地而起,爬升到150—200米高度,在彼得罗夫斯基公园上空掉过头,用全速从参观者的头顶上低低地掠过。我当时紧张极了。
突然,机场南面上空,在霍罗谢夫村一带有一条闪闪发亮的东西从飞机上掉下来,而飞机却未减速,平稳地下降,消失到许多树木的后面去了。脱落下来的东西在空中打着转,慢慢地掉到地上。
这使我大为震惊。飞机本来还应该再飞两三圈才降落到机场上的,然而它突然不见了。
大家纷纷问我:“出什么事了?”“飞机到哪儿去了?”但我无言以对。
我站在那儿等了又等,满以为飞机会立刻从树后面钻出来。我想:“这也许是飞行员开玩笑吧?”
可是飞机始终没有出现。这时大家都跑向汽车,顺着公路朝飞机消失的方向急驶而去。我们在路上听说,飞机已经降落在铁路货场地域的瓦甘科夫斯基墓地后面的某个地方。
我浑身打颤,心情痛苦万分,生怕飞行员和乘客出事。但是到了出事地点,我松了一口气,原来人员安全无恙,飞机也完好无损。
在堆满碎砖烂瓦和木柴的货场区内,一块小得可怜的空地上停放着一架飞机。既不见皮昂特科夫斯基,也不见马利诺夫斯基。他们走了,而飞机由一位民警看守。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走到飞机跟前,发现右机翼上的副翼脱落了。撕破的蒙皮一条条地挂着。副翼是在飞行中脱落的,我们在机场上看见的一条闪闪发亮的从飞机上掉下来的东西正是这个副翼。
幸亏飞行员在飞机几乎失去控制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对付它,并能出色而巧妙地将飞机降落到很小的场地上,才没有造成机毁人亡的重大事故。
我们把飞机分解开,运回工厂,仔细检查损坏的地方。检查结果发现,这次事故是由于设计错误造成的。的确这是一个错误。这架飞机比以前设计的飞机在速度方面跃进了一大步,因而需要特别仔细考虑副翼在机翼上的固定问题。
接着委派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次事故。这个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找我谈话,所以我只是后来才得知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其中大意是:“禁止雅科夫列夫从事设计工作,并通知政府:雅科夫列夫不配授予勋章(当时已呈请给我褒奖)”。
这样的结论是残酷的和不公正的。
委员会没有对飞机作出评价,也不认为这是苏联航空界的一项创新。不仅对我,甚至对跟我一道工作过的设计师和工人都报以一种怀疑的眼光,侧目而视。
这次事故之后,我未受到惩罚并非出于对我客气,而是由于工厂党组织的帮助和党中央根据我的申诉进行了干预,才没有完全剥夺我从事设计活动的权利。
在这段时间,跟我一道工作的这个小组一共有5~6名设计师和15~20名生产人员,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热心的航空爱好者。给我们用的地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家小工厂的仓库的一个角落。
地方虽然狭窄,然而我们在这里工作已是合法的了。我最亲密的助手是维甘特、西涅利希科夫、阿德列尔和谢赫捷尔。
但是,独立于中央设计局之外的这个青年设计小组的成长,使工厂领导感到不安,他们不让我们安然地在工厂的管辖范围之内占据一席之地了,决定撵走我们。不到两个月(1933年9月~10月)的时间内,我就接到工厂管理处的三道命令,要求腾出我们所占的工作场地,并且不另给其他任何可供我们小组工作的场所,而这个小组却早已办妥“轻型飞机小组”的合法手续,由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供给经费。
我至今还保存着这份要求我们搬离的正式通知书:
通 知 书(第142号)
根据厂长和厂长助理的命令,兹通知设计组组长雅科夫列夫同志:
命令您在今年10月10日以前交出你们占用的房屋——仓库,汽车库和设计小组的房屋。
同时通知您,从今年10月10日起禁止你们全体工人和工作人员进出厂区。
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
第×工厂管理处
亚历山德罗夫
1933年10月5日
我到底还是没有屈服,并为争取生存权利而积极进行了斗争。我向社会人士呼吁,向中央报刊申诉。
我们的不幸遭遇成了公众议论的话题。社会舆论奋起保护我们。《真理报》给了我们巨大的声援,不止一次地发表文章支持我们的设计工作。
令我感到不安的,不仅是我们设计小组的困难,还有小马力航空发动机这个带有共性的问题。
情况日益困难。怎么办? 厂长不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我决定向工厂的各群众组织求援。
首先我去见工厂共青团委书记萨沙·沃罗帕诺夫。
他仔细听取了我的意见,想了一下,然后说道:“我看,同名人,咱们去党委会找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去吧!”
党委书记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巴申是工厂里人所共知的一位为人正直、办事认真、有求必应的人。我们彼此早就认识,过去当他还在车间当木工的时候,就曾不止一次地帮过我制造第一架运动飞机。
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费多尔·费多罗维奇正坐在桌后,抽着纸烟,留心听着两位工人的谈话,并不时用他那聪慧而善良的目光鼓励谈话者。谈话刚一结束,他就给某人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工人们满意地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我知道你是为什么事情来的,谢尔盖耶维奇。”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说道。
他让我靠他近一点坐,接着开门见山地说:“厂长是个很固执的人,如果他不愿意帮你们的忙,你就拿他没办法。他在总局有得力的支持者。别人不会为你们和他争吵。不过我们总要设法使他受管束。谢尔盖耶维奇,我已考虑过解决困难的办法。我建议你马上去找党中央或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会给我们来电话询问情况,他们一定会来找我们,而我们支持你们。事不宜迟,因为他们正在撵你们,必须寻找达到目的的捷径。”
我几乎整夜没有睡觉:写好了一封信感到不行,又重写,这样一直搞到天亮。我拿着封好的信件乘车送到克里姆林宫。
圣母升天教堂门口的收发室收到了一封写着如下地址的信:“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扬·埃·鲁祖塔克同志”。
信递出去之后。还是觉得很不放心。有些人说我是枉费心机,另外一些人则断言,中央监委事情那么多,这件事得等上几个月,在这段时间里早把我们撵走了。
但是过了两天,鲁祖塔克派人打来电话,说最近几天他就要接见我。
过了一天,又来了电话说:“请来吧!鲁祖塔克同志午后四点钟等你。”
我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走进克里姆林宫。若是别的时候,我会好奇地仔细观赏克里姆林宫的奇景,但那时我心头只惦记一件事:但愿快点到达鲁祖塔克同志那里,得到他的帮助才好。来到接待室,秘书听我说明来意,请示后邀我到鲁祖塔克的办公室去。
我走进去有点胆怯,这是我头一次这样近地见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
扬·埃尔涅斯托维奇·鲁祖塔克那时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委主席和工农检察院的人民委员。一个中等个子的人从桌后迎过来,他身穿麂皮运动短大衣,浅色衬衫上结一条深色领带,戴着一副夹鼻眼镜。
他跟我问好之后请我坐下,发现我局促不安,便温和地说道:“请不要急。把您的情况慢慢讲给我听。”
鲁祖塔克同志取下夹鼻眼镜,用手帕擦了擦,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
我简要地汇报了我从事航空工作的经历,陈述了我的计划,并埋怨条件十分困难:“我国独立的设计局并不很多,实际上只有两个:波里卡尔波夫和图波列夫设计局。”我说道,“难道可以这么残酷无情地迫害我们这个青年航空爱好者小组吗?为了国家的利益,需要培育一些新的设计局,需要发展这一事业,而航空工业总局的官僚主义者们和我们工厂厂长却不懂得这一点,因此我才来到您这里请求帮助……”
鲁祖塔克在听我谈话的时候,一会儿摘下夹鼻眼镜,一会儿又戴上,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然后又坐下,记下一些什么。
后来,他开始详细打听我的工作,问我们制造的是什么样的飞机,为什么出了事故,有没有可能修好。
我不加隐讳地跟他说,我确实犯了错误,因而造成了事故,但这错误与我们的运动飞机在速度方面大大超过最快速的歼击机有关。我们在掌握快速方面已经向前迈进一大步,然而却要把我们撵出工厂。
“眼下你们在研制什么飞机?”鲁祖塔克问道。
“不久前,我们研制了一架旅客机,绰号‘空中汽车’。”
“‘空中汽车’吗? 有意思。可以坐它飞行吗?”
“当然可以,就是为载人研制的。不但可以坐人,而且我们的‘空中汽车’还可以在任何草地上降落。”
“哎,年轻人,您不是夸大其词吧?”
鲁祖塔克笑着说,“我住在哥尔克区尼古拉山下,您知道,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别墅就在这个地方。 您能飞到我们哥尔克去吗?”
“这得先去看看那里有什么样场地,飞机能不能降落。”我回答时有点发窘。
“我想用事实来考查一下你们的工作,”鲁祖塔克说道。
“请您到机场来吧!”我邀请道,“我们什么都拿给您看。”
“不,在机场上考查太简单了。如果你们能飞到我们那里去就好了。”
“那好吧! 我们试试。”
鲁祖塔克按一下电铃,把他的助手叫进来说道:“让雅科夫列夫坐车到哥尔克区去看看,飞机在别墅附近能不能降落……至于您的信,”他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马上拿到党中央和同志们商量一下,我想党中央会支持您的,并会对你们今后的工作作一些必要的指示。如果您能飞到别墅,那我们就在那里和您继续谈。”
鲁祖塔克跟我友好地道了别,我也很受鼓舞地离去了。
第二天,一辆汽车来接我和飞行员皮昂特科夫斯基一道去哥尔克。
鲁祖塔克的别墅位于莫斯科河的陡峭岸上,前面是一块面积不大的浸水草地,我们测量了这块草地的大小,来回察看有没有沟、坑或者土墩,最后确定这块场地完全适于飞机降落。
星期六,克里姆林宫来电话说,如果哥尔克的场地合适,鲁祖塔克将很高兴看见你们到他的别墅作客。
星期日一清早,我和皮昂特科夫斯基以及随机的机械员杰麦什凯维奇,就在机场上围着我们的飞机忙碌开了。到上午九点钟,一切准备就绪。
我和杰麦什凯维奇两个人乘车到哥尔克去迎接皮昂特科夫斯基。到了哥尔克,我们又察看了一遍场地,铺上白色对空信号布,并在草地边缘上点起篝火,然后等待飞机的到来。
皮昂特科夫斯基按约定时间从伏龙芝中央机场起飞,大约在十二点左右,一架红色单翼机摇晃着机翼超低空飞过鲁祖塔克别墅的上空。飞机飞了一圈之后,迎着风在草地上着陆了。
自然,几分钟后附近村子的人就开始汇拢到飞机旁来了。
不大一会儿,鲁祖塔克也来到现场。他祝贺皮昂特科夫斯基成功地飞到此地,同时也不掩饰他自己对我们竟履行了诺言的惊讶心情。
“坦白地说,我原来以为你们下不了飞行的决心。”鲁祖塔克承认道。
鲁祖塔克非常认真地倾听了我关于飞机研制情况的汇报,突然他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应当坐一坐您的飞机,看看‘空中汽车’是个什么样子。”
我以为扬·埃尔涅斯托维奇是在开玩笑,也就笑了起来,这当儿皮昂特科夫斯基却起动了发动机,打开飞机舱门,说道:“请吧!”
我慌了神。在非机场的条件下,用新飞机把一位人民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带上天去,岂可冒这样风险?!
“喂,您怎么啦? 勇敢点!勇敢点!”鲁祖塔克笑着说道。
无可奈何,我只好同鲁祖塔克一起进入座舱。
他饶有兴趣地把座舱看了一遍,然后坐下说道:“你们搞得很好嘛! 真正的汽车。怎么样,起飞吧!”
皮昂特科夫斯墓开动飞机,在草地上滑行,转到迎风的方向停下来。杰麦什凯维奇费了挺大劲儿才说服观众腾出场地让飞机起飞。
最后皮昂特科夫斯基加足油门——于是我们就飞上天了。在我们飞机的下面出现了尼古拉山、兹维尼戈罗德、莫斯科河套、田野和森林。
在佩尔胡什科夫上空转了几圈之后,回到哥尔克着陆。
“嘿! 好样的,我没有料到,太好啦!”鲁祖塔克高兴地说,“真正的空中汽车呀……”
他从机舱出来站到草地上,对这次飞行表示感谢,又把这架飞机夸奖了一番,随后请我们吃午饭。
我们怀着幸福的心情去到他的别墅。然而,刚刚在桌旁坐下,就听到一阵马蹄声,接着台阶上有人高声说话。
我向窗外望去,只见两个骑马的人飞驰而来。立刻有人进来把鲁祖塔克从桌旁叫走。
他出去一会儿马上又回到饭厅,拉着我和皮昂特科夫斯基的手,把我们领到台阶上。
“这就是违反规章的人,把他们带走吧!” 鲁祖塔克开玩笑地说。
我认出了这两位骑马人。一位是克·叶·伏罗希洛夫,另一位是阿·伊·米高扬。他们跟我们相互问好。
“我来看看是什么样的破坏分子,竟敢在这不合规定的地方驾驶飞机着陆,”伏罗希洛夫笑着说道,“这架红色飞机很显眼。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我俩就骑马赶到这里,看看现场发生了什么事。原来是航空运动员来了。鲁祖塔克同志,您在空中来得及画十字吗? 好样的! 你们是果敢的飞行家!”
我们整整一天都在鲁祖塔克同志家里作客。到傍晚黄昏时分,皮昂特科夫斯基才从哥尔克飞回中央机场。
我回到家,可是找不到自己的住处了,出了什么事了呢?
必定是出了大事。
我很快被叫到航空工业管理总局局长那里去。在接待室,我等了很久才被请进他的办公室。
在一张大写字台的后面坐着一位胖得出奇,满头黑发的人。当我走进来的时候,他既没跟我打个招呼,甚至也没请我坐下,用不友好的目光把我打量一下,就直截了当地言归正传了:“要把你们迁出工厂吗?他们做得对。可是这样一来…… 我已指示把你们的设计室和生产人员安置到列宁格勒公路(莫斯科到列宁格勒)边上—个铁床工场里。听明白了吗? 别抱更大的希望了,去吧!少到处去告状…… 不然的话…… 总之,去吧!”
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他已经事先通知了那家工场,铁床的生产仍然照旧。
我们的设计室就这样意外地出现在铁床工场里了。
这家工场安排在一栋不大的砖平房里。房间里的墙壁连灰都没有抹,土质地面上扔满厚厚一层铁棒和铁丝的料头,大概已经多年没有人清理了。工场周围地方,或者象这里人所说的工场院子,面积相当大,不过却盖满了木板棚子、马棚和敞棚,院子里垃圾堆积如山。
第二天,我把自己的伙伴们带到这里来商量。
一些最不熟练的工人在一间很小的、完全不适于生产的房间里,正在制造粗笨的“卡纳季基”牌铁床,这种铁床一直堆到天花板,占去了半个工场。
我们大家都拿不定主意:怎么办呢?
光有热忱和愿望不行,无论如何还得有个落脚的地方,哪怕很差也是自己的。这样一想,我们的疑虑也就解决了。我们都很年轻,渴望干一番事业,对航空这一行简直喜爱得了不得。我们看到无路可走,只好同意搬到铁床工场去。
我当时这样想:“只要站住脚,剩下的事就靠我们的双手了。”
自然,那时谁也没能料到这个小工场后来竟会变成一座绿树成荫、环境幽美的先进航空工厂。
我们找到了场长。后来发现,他是个善于钻营谋利的市侩。
伴随着爽朗的笑声,彼此自我介绍和握手之后,他马上甜言蜜语地絮絮叨叨地况了起来:“啊! 听说啦,听说啦! 那还用说,很高兴呀! 您的情况他们都给我讲过了。没什么关系,咱们一起干吧,我们的事业虽不大,但很有前途。我们年产一万张铁床,是条生财之道。”
“得啦,别光谈床了,现在该搞飞机了。”我说道。
“飞机嘛,当然喽……可是飞机这个行业怎么样?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飞机……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他用手在脖子上作一个杀头的富有表情的手势,“而床呢,这是可靠的行业:能给我们挣几万卢布的纯利润,光奖金就有……这不用我说,您自己也会看得出的。”
我马上明白了,跟这些唯利是图的市侩恐怕不会找到共同语言的,因此决定不跟他多费唇舌,先行动起来。
我们这个集体,设计师和工人总共只有35人,很快就搬到了铁床工场。
缅任斯基工厂准许我们带走制图用具、一些工具、几张木工台和钳工台。这些东西占去铁床工场的一半地方,另一半留给生产铁床。
我们把自己这一半初步整理好:清除了没用的东西,把墙壁抹上灰,并粉刷一新,还铺上了地板。摆好工作台、桌子和工具箱,然后就动手干起活来。
当然,这样的工作条件完全不适于制造飞机,就连制造我们正在搞的那样简单的小型运动飞机也并不合适。
为了制造飞机的机械零件,我们不得不把铁床工场的一台又破又旧的车床抢占过来使用。
青年车工马克西莫夫是位热心人,并且是一位车工高手,他把这台旧车床修理好,用它来车飞机零件。
木工赫罗莫夫、潘克拉托夫和钳工日罗夫、波兹德尼亚科夫也同样付出了很多劳动,他们在磨损了的旧的木工台和虎钳上造出了可安装在飞机上的合格零件。
屋子本来就很小,又用隔板隔开:一边安排设计师画图,拉计算尺,另一边则是一片噪声隆隆作响。
钣金工用锤子敲打着;木工又是砍,又是锯,又是刨;车床在轰鸣……
这一切我们都不在乎,我们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目标——在任何条件下都要造出我们预想的第一架教练机“乌特—2”(yT—2)。
可是仍然有人在阻挠我们的工作。有一次,他们竟不顾政府的指令,险些又把我们小组撤销了。
有一天,我出差回来,听说领导打算把我们搬到别的地方去,好让铁床工场扩大铁床生产。
我决心不顾一切去找《真理报》编辑部,反映这里的全部情况,请他们帮助。
“工场场长对飞机不感兴趣,”我说,“他需要的只是铁床的利润。”
经过《真理报》的干预,铁床的生产任务转到了其他工厂,铁床工场场址连同房屋全部归了我们。我们让制造铁床的工人改学飞机制造技术。
不久我被委任为场长。同志们跟我开玩笑说:“这位就是一年搞一万张床和一架飞机的工厂主。”
玩笑是玩笑,可是日子总算好过些了。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甚至弄到了一台真正的车床。
有一次,我认识了莫斯科地铁建筑工程局局长罗捷尔特,我把我们的困难告诉他。地铁工程局决定帮助我们,并以捐助的方式送给我们一台崭新的、非常好的“赶超”牌车床。
我们把车床领回来,但发现我们“机械加工车间”的门进不去,只好从窗户把车床搬进去。
有了车床以后,我们就把自己的工场改称为工厂。而这台车床,地铁建设者给我们的礼物,长期受到特别的尊重,许多年之后我们才把它作为纪念品转给一所工艺学校。
管理总局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别连科维奇被指派来照管我们的“公司”。他是一位朝气蓬勃、很有干劲的人,他同情我们,并帮助使我们的生产设备很快得到改善,工作条件搞得不错。
1933年过去了。我们在别连科维奇的帮助下,着手重新规划铁床工场的场地,兴建生产厂房,并纳入我们厂的总体建筑布局。
这个厂虽然困难重重,但我们已是自己工厂的主人,我们研制了三种装小马力发动机的飞机,这对我们这个小小的设计集体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决定了我以后的设计命运。
在铁床工场里研制的“阿伊尔-9”、“阿伊尔—9比斯”和“阿伊尔—10”都是享有盛名的双座“乌特—2”飞机(乌特——教练的意思,是教练两字的字头)的原型机。后来曾用这种飞机对成千上万的飞行员进行过初级飞行训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成了卫国战争的英雄。
《真理报》仍然和从前一样,非常支持我们。
1934年8月,《真理报》和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共同组织了第一次“阿伊尔-6”轻型飞机小队的大规模体育运动飞行,航线是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莫斯科。这次长途飞行非常成功。
1934年8月16日, 《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生产轻型飞机和地区航线飞机而奋斗》的社论,文中说:
“这次轻型飞机由莫斯科至伊尔库茨克的长途飞行虽然在各方面都完成得很出色,但与现在航空的卓越成就相比,当然就显得很逊色了。然而这次长途飞行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为苏联的轻型飞机开辟了道路,社会舆论给这种飞机一个恰当的绰号‘空中福特’。
苏联设计生产的、安装国产100马力小型发动机的‘阿伊尔—6’轻型飞机小队非常完满地执行了交给它的各种任务。尽管天气条件极为不利,而这四架飞机五个昼夜飞行了35个小时,航程4,263公里,没有发生过一次事故或损坏,也没有一次迫降,现在已安全返航了。
当我们为苏联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和《真理报》组织的这次长途飞行作总结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轻型飞机的普及工作已经有了开端,这种飞机在我国有广泛的发展前景。以筹备航空节的形式进行的这次长途飞行把广大社会人士的注意力已经吸引到轻型飞机问题上来了。同时这次飞行也十分令人信服地证实了阿伊尔型飞机的可靠性和耐航力。
这种时速150公里的飞机,结构非常简单,易于驾驶,座舱布置舒适,对起飞、着陆场地的要求极低,每飞行小时的耗油量为数不多,几乎任何棚子里都可以停放,可容纳三个人和他们的行李。这样的飞机在我们各加盟共和国、边区和州最受欢迎,对那里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可起到重要的助手作用。”
四架“阿伊尔-6”飞机顺利地飞了近一万公里的航程,没有发生任何事故。中央各大报的记者参加了这次长途飞行。
1934年8月25日,《真理报》在题为《苏联的空中福特》的社论中写道:
“8月18日,正在热烈庆祝航空节的时候,‘阿伊尔—6’轻型飞机小队出现在土希诺机场上空,然后下降着陆,以此来结束这次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的长途飞行。
正当成千上万人的会场上的注意力被歼击机空战的诱人场面所吸引的时候,轻型飞机长途飞行的参加者一到,大会就热情洋溢地欢迎起他们来。这说明,轻型飞机在我国很受欢迎。阿伊尔型飞机长途飞行的参加者一致肯定这一结论,因为他们每到一处,人们都对轻型飞机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对轻型飞机之所以普遍感到兴趣,不可能是别的,而是因为大家都确实感到需要它。我国各边区和州的各级组织需要用轻型飞机来与本区和本州内任一居民点迅速而方便地取得联系。我们的经济管理机关要想高效能地领导企业,也需要轻型飞机。我们航空俱乐部的青年以羡慕的眼光看着轻型飞机,因为他们需要用这样的飞机进行训练、宣传鼓动和旅游飞行。人们焦急地期待着在民航地区航线上能有轻型飞机。
轻型飞机就是‘空中福特’。这如同只有在轻型汽车出现之后,汽车才成为普及的东西一样,小功率飞机也为广大各阶层居民提供了掌握飞机的可能性。轻型飞机的广泛使用,对提高文化水平的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对巩固国防的作用也是巨大的。给国家提供足够数量的轻型飞机是当前最迫切的需要……
应当说‘阿伊尔—6’并不是苏联轻型飞机唯一的代表。我们还有许多这种类型的轻型飞机。我国的设计师们对轻型飞机的问题愈益发生兴趣,因此可以指望他们研制出结构更为先进的新型飞机。然而,根据参加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莫斯科的飞行的全体人员的共同评定,‘阿伊尔—6’飞机出色地经受住了这次考验。现在的问题是看航空工业如何安排好轻型飞机的成批生产。”
进入1936年的时候。我们设计室在原铁床工场场址的地位已相当巩固,可以拿出资金来建设很好的装配车间和非常漂亮的设计室了。我们这个集体已与生产“阿伊尔—6”、“乌特—1”、“乌特—2”飞机的几家批生产工厂建立了联系。我们创办的这个企业。
后来不仅成为运动机整个系列、也成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起到自己的作用的雅克作战飞机系列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