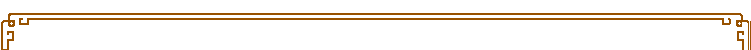我们兴高彩烈地庆祝了1940年的十月革命节,因为我们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已走上正轨。10月8日晚上是在莫斯科近郊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别墅里度过的。
正玩得很开心的时候,人民委员走过来对我说道:“叫您赶紧到克里姆林宫去找莫洛托夫,我已经要好车了。”
克里姆林宫静寂无人,政府机关在节日都不办公,人民委员会的走廊里也没有人。
这是我第一次到莫洛托夫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与他单独见面。
在此之前,我曾不止一次地和他在各种会议上见过面,而且经常是在斯大林那里,他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一起商讨各种问题。
他一般是坐在斯大林左手一边,右边是伏罗希洛夫,长桌两边则坐的是日丹诺夫、米高扬和其他人。
他面前总是放着随时带在身边的装有许多外事文件的公文夹。他一边看阅文件,一边作批语,有时只在擦拭夹鼻眼镜时才抬抬眼,为的是让我们相信他在仔细倾听。
莫洛托夫经常参加讨论我们的航空问题。
向我问好并让我坐到他对面沙发椅上之后,莫洛托夫便通知说,我已被列为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去柏林与希特勒谈判。
“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问道。
我很不机灵,而且蠢笨地回答说:“遵命。”
莫洛托夫打断了我的话,不满意地说: “您会说人话吗? 您愿意不愿意去?”
我马上醒悟了过来,并回答说; “非常感谢对我的信任,我当然愿意去。”
“噢,那是另一回事,”他说,“那么,您必须在明天晚上九点钟到白俄罗斯车站,我们一起去柏林。这是斯大林同志的指示。”
“怎么明天就要走?”我惊奇地问道,“可是我还没有出国护照,而且也毫无准备。”
“您什么都不用担心,一切都会有的。一只手提箱和一件干净衬衣总能够找到吧?…… 对您再也没有别的要求。那就明天晚上九点整去白俄罗斯车站……”
第二天,我驾着自己的汽车按时来到白俄罗斯车站,好不容易才穿过已经戒严的广场。车站入口处对面停放着许多插有小旗的使馆汽车。我既没有车票,又没有任何证件,但终于还是顺利地到达了月台。月台前停放着一辆专用列车。
我们是按规定的时间动身的。
可是火车刚开十来米,突然剧烈震动一下便停住了。怎么回事?!
几分钟以后又开动了,可是还未到月台尽头,火车又第二次停住了,而且震得更加厉害。铁路员工奔跑着,忙乱了一阵,原来是发生某种不顺利的事了。
发生了什么事?
原来德国大使冯·舒伦堡伯爵也乘坐这挂列车。两次都是他拉紧急制动阀使列车停住的,仅仅因为大使馆没有在开车之前把他打算在柏林下车时穿的礼服送来。
火车最后还是没有等到礼服送到就开动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因为给冯·舒伦堡送箱子的使馆汽车没有特别通行证,所以没让它通过车站前面的广场。当了解到是给舒伦堡送的礼服时,便派了两辆轻便汽车追赶火车,而且要赶在列车前面,以便在一个中间站将伯爵的行李装上火车。
这件事发生在十一月,大地表面已冻上一层薄冰。两辆汽车沿着莫扎伊斯基公路疾驰,其中一辆汽车载着行李,另一辆作后备。第一辆车子不知是在戈里琴诺还是在古宾克就出了事故,便将箱子转到了第二辆车上继续前进,大概到了维亚兹玛就把大使的箱子送到了神情极为不安的伯爵手里。
我们在柏林受到了符合政府代表团外交级别的尊敬和欢迎。
当火车进入安加尔车站时,那里已聚集了许多欢迎的人群,其中有希特勒德国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陆军元帅凯特尔。仪仗队排着整齐的队列,乐队奏起了《国际歌》。
我们所住的柏尔维尤宫,一切都预先作了“周到”的安排。除了鲜花、水果、矿泉水、柏林旅游指南和各种广告外,殷勤的主人还关心我们的“精神食粮”,在桌子上的水果旁边放着一本《人民艺术》画报,是用非常漂亮的铜板纸印的。封面上画的是两名威风凛凛的德国士兵,一只手拿着手榴弹,另一只手握着手枪,背景是浓烟滚滚的华沙废墟。
我翻阅了几页。记得有这样一幅画面: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树下,有一个快要死去的德国土兵跪着把头垂在一位天使般的、笃信宗教的姑娘手上。这一切都是用表示“阴间”的那种明暗色调描绘的。姑娘温柔地抚摩着那个快要死去的人的头部,而将要一命归天的土兵面部表情却很怡然自得。这幅画的意思是,为元首而死是德国人的最高天职。
下面一页则是一幅色彩鲜明的插图,画的是炮手班正在一尊德国重型火炮周围忙碌着。远方天际,则是一片灯光辉煌的建筑物。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种相当明显的暗示。可是又不得不向我们表现出外交上的殷勤样子,客气地交谈,微笑着在宴会上相互举杯致词,与自己邻座的人碰杯。
好象是到达的当天,就在“凯撒霍夫”饭店为我们代表团举行了欢迎宴会。
我们来到这家豪华的饭店时,前厅闹哄哄地,就象蜂房一样。许多身穿燕尾服、晚礼服和挂着勋章与奖章的制服的德国人挤满了大厅。通过敞开的门可以看到巨大的摆着漂亮餐具的桌子。大厅入口处的墙上,贴着每位客人的座位图。规定的时间一到,便邀请大家入座了。
宴会的主人里宾特洛甫部长左右逢源,殷勤地微笑着。我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并和自己的邻座点了点头。在我们每个人前面的餐具旁都放着一张菜单和注有被邀请者姓名与官衔的名片。
我想知道谁坐在我旁边,便斜着眼睛向右边瞧了一下,原来是德国最著名的工程师和军事技术装备的组织者之——托德将军的名片。
我又瞧了瞧坐在我对面那个人的名片,那是曾任德国副首相的冯·巴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冯·巴本不知道是驻美国的陆军还是海军武官。
当他举起高脚酒杯转向邻座的人,并力图在自己面部表现出象是微笑的样子时,他那双平淡无奇的眼睛甚至毫无表情。他和所有的法西斯头目一样,一直到死都是个伪君子。
五年之后,当冯·巴本被英国人俘获时,他还谦逊地问道:“你们想从我这老头儿这里知道些什么呢?”
战后国际军事法庭对于作为德国主要战犯之一的巴本进行了审讯。
坐在我左边的人是位年迈的海军上将,我已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嘴里的牙都掉光了,说话含糊不清,他突然和我用俄语说道:“我懂你们的语言,您不感到奇怪吧。我1927年曾担任过驻莫斯科的海军武官。您可能记得当时发生过刺杀我们大使馆参赞的事件。打那开始我就离开莫斯科了。现在我在外交部任专员。”
宴会忽然中断,传来了急促的警报器声。主人们感到惊慌,一个个都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德国军官帮我们转移到柏尔维尤城堡的防空洞。我们到了大街上。这是个明亮的月夜。英国的飞机在高空发出嗡嗡的声音。无数的探照灯光在空中搜索,竭力想找到它们。高射炮轰隆响着。
探照灯光逐渐消逝了,高射炮的射击声也随之停止了。
当时和德国比较,英国空军还很弱,飞机数量也不多。空袭时,柏林居民往往只感到受了一次惊而已。正如后来所发生的情况一样,英国飞机并未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不幸。
第二天是希特勒接见。
我们从下榻的旅邸——柏尔维尤宫出发,沿着胜利林荫大道,经过勃兰登堡门,顺着温特尔—登—林登大街向右拐,便到了威廉街。在这条街上有一条通道通往新帝国总理府,人们称这里为宫庭,也就是希特勒的官邸。它在柏林市中心占了整整一个街区。
大门向我们四敞大开。我们的汽车开进了新总理府里院。院子呈长方形,四周围着用灰色石板砌成的院墙,高度一样,墙上有一些方形窗口。院内也用同样的灰色石板铺得平平的,就象棋盘一样,给人的印象仿佛走进了石头盒子似的。只在对着大门口的一面墙上,有一道庄严的二门,装着两扇带镜子的门。
二门两边和大门口一样,都有党卫军分子象石头雕像似地把守着。他们身穿浅绿色制服,头戴有法西斯帽徽的钢盔,挂着党卫军的特殊徽章:一个头颅骨和两根交叉的骨头。
将我们领到前厅后,便请我们坐下。这里陈设的家具非常讲究。前厅的地板整个铺上柔软的红地毯,木器都很名贵,墙上挂满了许多著名画家的画。几个头发梳得很光的军人,毕恭毕敬地互相在低声交谈着。他们走来走去,没有一点响声,有时用鞋后跟咔嚓一碰,表示法西斯的敬意。
庄严、肃静、低声说话———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为了从心理上训练那些需要在元首面前“出现”的人。
等了5~10分钟,同样用很低的声音传下一道命令。鞋后跟的咔嚓声碰得更加有力。陪同我们的外交官员使劲弯着身子,向通往另一房间的拱门作了个手势。我们明白,这是在请我们过去。
我们站起来,向另一房间走去。在房门口我意外地见到了阿道夫·希特勒。他站着在等候我们,把我们让进屋后,便和大家一一问好。陪同人员把我们每个人都向他作了介绍。跟在希特勒后面的是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希姆莱、陆军元帅凯特尔和莱伊。
希特勒穿的是法西斯党徒的传统服装:咖啡色上衣、黑领带和黑裤子。他的面部毫无表情。臭名远扬的额发,平淡的灰色眼睛,病夫般的淡黄色面容,湿润而肥厚的手握着没有力量,所有这一切给人一种不愉快的印象。握手时他总是扬着自己直勾勾的眼睛,很快就转到另一个人了。
站在旁边的约希姆·里宾特洛甫与他形成鲜明的对照——高高的个子,穿得很整洁。他握手很有力,时间也长,留心地看着对方的眼睛,脸上带着非常礼貌的微笑。给人的印象是:他认识您,并想对您表示特别的好感似的。看来这是由于多年的“外交活动”,使他练就了这样一套社交手腕。
接着和约瑟夫·戈培尔寒喧。他是个瘸腿小瘦猴,我们从许多漫画里就认识,与画里的像很相似。他的穿着与希特勒一样:咖啡色上衣和黑裤子。他有一对蛮横无礼的、不断转动的小眼睛,一副满是粉刺疤痕的黄色面孔,头发梳得溜光,搭拉着耳朵。牙齿不好,满口病牙。
站在戈培尔后面的是所谓“劳动战线”的领导人罗伯特·莱伊。他是个身材魁梧、两腮红润的男子,双下颏。后脑勺有三道摺子,面颊上有个血红色的伤疤,嗓音嘶哑而粗野,象个典型的屠夫。一对湿润的蛤蟆眼,脸上油光光的,手指头短胖得象刀切的一样。他竭力装出一副与我们相识感到非常满意的样子,他不停地微笑着,而且还发出一种显然是感到满意而又莫明其妙的声音。
总参谋部的代表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的脖子上戴着一枚铁十字勋章,是个典型的普鲁士人,已上了年纪,高个子,面部表情象石头一样呆板,眼睛冷淡而生硬,也不象别人那样喜欢说话。他打招呼也不作声,只用鞋后跟碰一下发出咔嚓声来表示。
秘密警察头子,德国头号刽子手,令人恐怖的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和达哈乌等集中营的组织者海因里希·希姆莱给人一种极端可厌的印象。他身着党卫军军官服,即灰色制服,丝绒领上挂着传统领章:一个颅骨和两根交叉的骨头。小脑袋,留的小平头,尖鼻子,长着象蛇嘴一样的薄嘴唇,一对小而冷淡的鼠眼,架着一副夹鼻眼镜。我甚至无法形容他是个什么样子。有时感到希姆莱看人,就象蟒蛇一样不眨眼睛。他的神色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全班人马就只差戈林一人,因他当时不在柏林。
相互作了介绍之后,希特勒便请我们在一张布置得富丽堂皇的摆着鲜花的餐桌入坐,每个人的座位都是事先规定好了的。靠墙的右面,站着10~15个服务员,都垂手直立在那里,全是些年轻人,个子一般高,肤色也一样——都是淡黄发男子,眼睛的颜色都一样,甚至连彼此的相貌都很相象。全部穿同样的服装——银线绣花短上衣,浅灰色裤子,白胸衣和黑色蝴蝶式领结。这些服务员倒是非常象军人,他们工作得如此协调,动作也非常机械,而且都是经过训练的。
专有一位服务员伺候希特勒。他是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军官,个子高高的,也是位年轻的淡黄发男子:有一对蔚蓝色的眼睛。所有这些人,包括给希特勒端菜的军官在内,都是最纯的阿利安人种的化身,这就是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的“淡黄发恶棍”。
这些“淡黄发恶棍”与德国法西斯的首领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戈培尔都决不能算作与他们是同一血缘的人种。
希特勒及其幕僚们对我们非常殷勤。
午宴是在正常外交程序的气氛中进行的。聊的都是些最空泛和不着边际的话。和德国所有其他类似的招待会一样,我在这里也听到了对俄国作曲家柴科夫斯基的优美音乐、莫斯科大剧院俄国芭蕾舞艺术(里宾特洛甫曾在莫斯科观看过《天鹅湖》),俄国人内在的高尚品质、
“举世闻名的”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的一片赞扬声。一句话,一切都是在通常的外交礼遇中进行的。
我在午宴上发现,希特勒是个吃素的人:有人用专门的带盖的大盘子给他端菜,放到桌上之后才掀开盖子。盘内放着几个专用的银制食盒。每个食盒装着不同的食物:有稀粥、新鲜蔬菜、沙拉、煎菜和其他一些素食饭菜。
服务员们给所有出席的人都是斟的酒,只有希特勒一个人饮的是从特制瓶子中倒出的一种什么水。看来,他既不喝酒,也不抽烟。
在午宴上,人们就告诉我们说,新的帝国总理府是办公的地方,希特勒住在两间一套的很普通的住宅里。这个伪君子装成一个谦逊的、正派的德国人,只有中等居民的要求。
在其他的场合,他又竭力给人造成一个伟人的印象。他在军事检阅中,在大群突击队和法西斯匪徒们面前,发表了许许多多讲话(已拍成电影),在他讲话时,千方百计用自己的外表、步态、手势和历史性的演说让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形象是伟大的。
希特勒的行动经常象小丑那样滑稽可笑。后来我在电影上看到,当与维希政府的投降分子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贡比臬车厢里签订停战协定时,他甚至还在装腔作势。
正如大家都知道的,1940年11月在柏林进行的苏德谈判,时间不长,也无结果。以莫洛托夫为首的整个代表团都返回了莫斯科,却把我留在那里又呆了两个星期。因为给了我一项任务,要求我利用自己在德国逗留期间,了解我前几次所参观的几个航空工厂的情况。
我成功地会见了好些个德国航空专家,并再一次去到愿意让我们参观的几个工厂。象前几次参观一样,我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希特勒分子为什么把最保密的军事装备部门之——本国的航空工业做这样坦率的介绍?
后来他们自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一次,我们应邀参观海因克尔在柏林附近的奥拉宁堡航空工厂。这是一家很好的工厂。过去的确没有过一下子就让我们参观某个工厂的情况。我们想参观某个企业,都得事先告诉他们,然后才把我们送到那里去,所看到的一切自然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参观完这家航空工厂之后,厂长要我在贵宾留言簿上写下自己的观感和评语。
我感兴趣的是,在我之前都有谁在上面留过言。原来在参观这个工厂的外国人中,我们并不是第一个。世界上几个最大的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的许多著名航空活动家都参观过这家工厂,并留下了自己的评语。我发现美国有名的飞行员林白也到过这里,而且留下了热情洋溢的题词。
厂长非常欣赏法国空军司令维也芒将军的亲笔题词。此人是在对德战争开始前不久访问这家工厂的。他写道:“这是一家出色的,世界上最好的工厂。它不仅使工厂的建设者们,而且使整个德国空军都感到自豪和光荣。”
正当我在念的时候,厂长狡猾地看了我一眼。
我念完后问道:“您的工厂究竟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给予这样的评价?”
厂长回答说:“问题在于维也芒将军战前在我们这里呆了一个半到两个月的时间。他及其一行都参观过我们的工厂并称赞德国的空军。不过看来他们没有得出恰当的结论,因为两个月之后法国人竟和我们打起仗来了。”
这样就使我明白了他们之所以让法国将军参观德国这家最好的飞机制造厂,是为了证明德国的空军实力要比法国的强得多。
他们吓唬过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吓唬过美国人,还想吓唬我们。看得出来,他们是企图用自己的实力来吓倒我们。不仅引导人们要尊重德国的技术,更主要的是想在我们身上播下对德国军用飞机的恐惧感,为他们征服别人打下基础:让人们在希特勒德国的实力面前胆战心惊,以便摧毁其抵抗的意志。
回到莫斯科时,我好象直接就从车站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了。
斯大林对德国的航空事业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每当我从德国参观回来时,正如读者所注意到的那样,当天就把我召到他那里去。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
我在客厅遇见了莫洛托夫,打了招呼之后,他便笑着说:“喂,德国人! 现在人家都在议论我们和您了。”
“为什么? 维亚契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
“怎么不是! 我们和希特勒吃过饭没有? 吃过。向戈培尔问过好没有? 问过。应当悔悟了。”莫洛托夫开玩笑地说道。
这天晚上讨论了许多问题,大部分都与航空没有关系,可是并未放我走,间或还问我这次在德国看到什么新东西。
和以前一样,斯大林最关心的问题是,德国人在出售航空技术装备时是否欺骗了我们。
我报告说,通过这第三次参观,现在可以坚信,德国人给我们看的,都是他们航空技术装备的真实水平。我们所购买的样机:“梅塞施米特—109”、“海因克尔—100”、“容克斯—88”、“道尼尔-215”和其他飞机都反映了德国目前空军装备的状况。
事实上,后来的战争也证明,除了我们所掌握的上面几种飞机之外,在前线只出现过一种新歼击机——“福克·沃尔伏—190"。可是这种飞机却使他们大失所望。
我坚定地认为,德国人当时已被征服欧洲所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料到俄国人能够与他们匹敌。他们深信自己的军事技术优势,即使公开了自己的航空机密,也不过是想如何更有力地战胜我们,动摇我们的信念和吓唬我们而已。
夜已深了,在我回家之前斯大林说:“您去组织我们的人对德国飞机进行研究,把他们的飞机和我们的新飞机作个对比,学会揍它们。”
战争开始前一年,五架“梅塞施米特-109”歼击机、两架“容克斯-88”轰炸机、两架“道尼尔-215”轰炸机以及一架最新的歼击机“海因克尔-100”已运到莫斯科。在这之前,我们就已拥有自己的具有竞争能力的歼击机“拉格”、“雅克”和“米格”,强击机与轰炸机“伊尔”、“彼—2”。
我们在德国逗留期间,英国与法国的报刊象一年之前一样,又拼命地大喊大叫起来,指责我们与希特勒勾结。他们总是带着疯子般的顽强劲儿,梦想德国人跟俄国人打起来,期待着俄国被打垮,德国被削弱得一蹶不振。可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形势,苏联政府宁可进行谈判。多争取到一天和平,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利的。
争取时间,对我们航空事业尤为重要:终于使我们能在1939—1940年内创制出一些新的非常现代化的作战飞机,并于1941年以前投入了成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