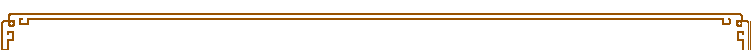间或刮起一阵阵风,撞在房墙上,又转过弯来,在街上乱窜,打着转,雨夹着湿雪倾泻下来。冰冷的水滴滚下脸颊,顺着下巴流到衣领上。走路人把帽子一直扣到额上,耸着肩膀,侧身走路,把最能挡风的部位对着风。
在这种天气里,德国人没有射击。
涅瓦大街的一家药房里,走进了个穿帆布雨衣的,中等身材的男人。那人四处张望了一下。
一缕白日的亮光透过唯一没有钉上板的窗子射进来。靠窗有个出纳亭;左面角落里设了个机枪火力点,枪眼塞了破布:它的对面是橱和柜台:左边玻璃档板后,有个穿白色工作服的胖女人在记录药方,每写完一张,就拍一下笨重的镇纸尺,声音很响。女出纳员则在看报。
那男人不慌不忙脱下湿帽子抖了抖,走到了接方员跟前。
“来吧,您有什么事?”女人伸着手问。
“我要找沙尔科夫斯基同志。”女人看了看来访者,一声不响地走到玻璃门后边,透过玻璃门看得见里边一些放着各种各样瓶子的架子。很快她回来了,一句话不说又重新抄写起来,不时拍响着桌子。男人等了大约5 分钟,玻璃门敞开了,一个满脸皱纹、戴夹鼻眼镜的小老头子急速奔到柜台跟前。
“您叫我吗?”
“如果您是沙尔科夫斯基,那就是。”
“怎么回事?”
“有人托我找您。‘格里戈里·彼得罗维奇病了,要六包阿司匹林粉。’”来访者平静他说。
出于突然,沙尔科夫斯基哆嗦了一下,但随后就镇定下来,咕哝着:“多么不愉快的事!但愿不是什么重病。感冒了,还是别的病……这样健康的人……请等一回儿。”
等不多久,老头子很快就拿着个小盒子回来了。他向胖女人要了支蘸水笔,在盒子上写了几句活,接着走到柜台尽头。中年男人走到他那儿。
“这就是药粉,”沙尔科夫斯基递过盒子低声说,“他真的病了吗?”
“如果病好了,11月20日左右他会亲自来,”来访者也压低声音说,“转告他,信我按原来地址送去了。对他说,一切顺利,没有变化。”
“好,您在城里很久了吗?”老头于更低声问。
“节日那几天来的。”
“片子没有带来吗?”
“什么片子?”采访者不解。
“唱片。”
“啊……没有。除了信,什么也没有。”
“您安顿得怎么样?”
“没有什么好安顿的,一切都很顺利。”
“晚上来一下,地址写在盒子上。”
“我忙得很……不过尽可能去。可以走了吗?”
“走吧,走吧……”来访者把盒子放进口袋,不慌不忙走出了药房。
沿着小涅瓦河河岸,离桑普森尼耶夫桥不远,走着一个支拐杖,穿件没有肩章皱巴巴军大衣的年轻人。看来,他还没有习惯使用拐杖,脚步挪动很不稳。恶劣的天气使他更加受累,右面身体沾满了雪,不过他对此倒并不在乎。
残废军人转弯进了一扇大门,那是一幢外表看来很漂亮的大房子。整个院子堆满垃圾,他站定身子,踌躇了很久,始终下不了决心从砖上爬过去。
背后传来了响声。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腋下夹了个旧公文包,正在跺脚,抖掉沾上的泥上。
“这些该死的东西,”她用手掌擦擦湿漉漉的脸,咕哝说,“同志,您是来这里找人,还是来避雪的?”她看见残废军人问。
“有事来这里,可就不知怎么克服这些障碍。”
“您到几号住宅?”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收到了通知单,这就是说应该先去房屋管理员那里。”
“啊哈!我就是管理员,通知单拿来。”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接过通知单,把它看过后乐坏了。
“来了!昨天住宅管理科对我说过几次,我一直等着。您从军医院里出来吗?稍等会儿……”
她灵活地沿着砖块走到底楼的一扇窗前,用拳头砰砰地敲了敲窗框。台阶上跳出个身材不高给吓坏了的女人。
“我在这儿!玛丽亚·安德烈耶芙娜。”
“喂,你来帮这位同志登上33号住宅。”
“马上就来!”
女人在入口处消失了,但管理员刚走到残废军人身边,她就穿着短棉袄,包上羊毛头巾又出现了。
“你们这里比前线更糟,”残废军人说,“别说是弹片,砖块和玻璃也会伤人的。”
“不要说了!没有吓死才洁着。”残废军人笑着看了看管理员,恐怖的感觉与这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粗气的女人是不相称的。
来了个扫院子的女工,于是他们两人托着残废军人的两只胳膊,轻而易举地搀过一堆堆垃圾,以后就顺着楼梯上了三楼。
管理员又很不礼貌地用拳头砰砰敲响了33号住宅的门。
住宅对面的门开着,从那里飞出白色的石灰粉,像一团蒸汽一样。
“工人在那儿修理住宅,”管理员解释说,“您的房间很完好,甚至还有半扇玻璃窗。”
这时门后传来了响声和一个女人的声音:“外面是谁?”
“是我,房屋管理员。开门。”
一个不很年轻的瘦女人开了门。
“您看……尽抱怨说没有男人害怕,”管理员说,“这不给你们送来了一个男人,而且不是一般的,是个英雄,卫国战争的荣誉军人。当心,别欺侮他。”
“哪儿的话,玛丽亚·安德烈那芙娜,怎么可以?我们的男人也在前线,您却说这种话……”
“好吧,不是每个手指头都是一般齐的。”
管理员打开了封着的房间。把撤退人员留下的家具编了号,又从新房客那里要了个”临时保管”的字据,然后讲清何时、何地和怎样可以碰到她,就道声好,走了。
残废军人和两个女邻居留了下来。
这些日子里,列宁格勒很少残废军人,对于失掉亲人打外区搬来,忍受许多痛苦的劳动妇女来说,这样一个新房客的到来是再好没有的事了。心地善良、富于怜悯心的俄罗斯妇女终于找到了照顾的对象。一转眼工夫,桌上已经放好了热茶和简单的点心。残废军人这么年轻就跟拐杖相伴,特别触动妇女的心,所以她们争先恐后提供自己的帮助。
“多谢你们,我疲倦了,想睡觉。晚上我们再谈谈,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他挨到沙发上坐下说。
看他除了军大衣外什么也没有,妇女们拿来了枕头和被褥。天黑以前的照顾这才算结束。
下午,天有了好转。风静了点,雨也停了,雪开始下小了,没落到地面融化以前,雪花久久地在空中盘旋,仿佛在给自己选择一个落脚的地点。
谢尔盖·德米特里那维奇·扎维亚洛夫刚与女儿吃过午饭,准备照常实验,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是扎维亚洛夫。”
“谢尔盖·德术特里耶维奇,请到我这里来一下,”他听出了厂长的声音。
“现在吗?”
“是,如果可以的话。”扎维亚洛夫对占用工作时间发了几句牢骚,就去办公室了。厂长笑着迎接他。
“坐下,别生气。事情很重要,您得与主任工程师去莫斯科。”学者皱紧了眉头。
“为什么?”
“去总局报告。”
“这真是新闻!”扎维亚洛夫极为惊讶,”怎么这样……突如其来。”
“错了,谢尔益·德米特里那维奇,完全不是突如其来,已经过了5 天到7 天。”
“可是我的信管怎么办呢?”
“主要就是为它才去的。那里您会知道你们技术的最新消息,阐明一切可能性。在我们的仓库里反正原料很少。”
“这是另一个问题,为这个不一定要我去莫斯科,有供应科嘛。”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您的威信很有作用,如果您亲自跟首长说一说……”
“懂了……唉!没有料到,没有料到。”
“您不是准备夏天去科学院吗?”
“不是那个事,报告使我头痛。就是说,又得准备。”
“那又怎么呢?有的是时间。女打字员我给您安排。”学者摸了下小胡子,作了最后拒绝的尝试。
“难道非我不行吗?”
“怎么也不行。我们对派谁去动了很多脑筋;我们不想打断您的工作,但是您也明白,这在眼下是多么重要。”
“一般说来,借此机会出去一次,这也不坏。完全不坏,”化学家沉思着说,“对,不能老是闭门造车。我已经三年没有去过别的地方了。是的,三年缺一个月。在化学里有许多新东西——这很自然。科学界现在工作很卖力……可出版物却很少。如果一定要我去,我也只好去一趟。写出差证明吧,瓦列里·库兹米奇。那我乘什么走呢?”
“乘飞机。”
“乘飞机!哪儿的话!”学者惊奇起来,并突然推论说,“我不会跳降落伞,一次也没有跳过。”
厂长笑了。
“41年,”他说,“妻子对我讲,有一个女公民断言说她在排队时看见一个法西斯分子乘降落伞落到他们的屋顶上,看了看他要的东西,又飞走了。还一口咬定她是亲眼目睹的。”
扎维亚洛夫哈哈大笑起来。
“乘降落伞飞走?奇迹!这应当去对小孩子说。”他们拟定了一个大概的报告计划,记下了一系列应在临行前“详细研究”的问题,准备到莫斯科去说明,然后他们彼此都很满意地分了手。
特里福诺夫完成任务回来,登上自己的办公处,给首长打了个电话。
“中校同志,特里福诺夫报告,”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回答后,他说,“刚到。”
“一切顺利吗?”伊万·瓦西里那维奇问。
“好像是。”
“‘好像’是什么意思?”
“这里有一点没有料到……”
“请来一下。”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穿着普通的西装,好些地方抹上石灰,他刚刚去了正在进行修理的扎维亚洛夫的住宅,还没来得及把衣服弄干净。助手的电话使他十分担心。
特里福诺夫走进办公室,把从药剂员那儿拿来的药粉放到桌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盒子推过一边。
“喂,您那儿怎么回事?”他问。
“按顺序讲吗?”
“不,先说说什么没有’料到’,您怎样回答。”
“沙尔科夫斯基间我,有没有带来国声机唱片。我回答没有:说除了信,什么也没带来。”
“嗯,那后来呢?”
“再没有什么了,叫晚上去一次。”
“是这样!”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拖长声调说,“唱片。记得很清楚,卡扎科夫关于唱片什么也没有说。我看了全部记录,这是新情况,好,现在请坐下,把一切按次序讲。”
听完造访药剂员的详细报告,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把写在盒上的地址同他那儿已有的地址核对了一下。
“我们原来把沙尔科夫斯基忽略过去了,特里福诺夫同志。那是个老牌间谍,我得到了很不寻常的材料。”
“是,老家伙看来很有经验,“特里福诺夫同意说。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从盒予里拿出了阿司匹林粉,打开了其中的一包,闻了闻。
“阿司匹林,”他慢腾腾他说,他原以为其它什么东西。
“关于唱片我自己来弄清楚,现在您需要设计好扎维亚洛夫住宅里的信号装置。铃声不适合,得是一种声音很轻的小汽笛……又不能经过梯台,马尔采夫可能注意到。”
“容许提个建议。”
“提吧。”“装作旧天线!经过窗子拉到外面,搭在屋顶上,而另一头通到布拉科夫那里。”
“不知道行不行……到现场去看一下。那儿二层楼上架设着电线,或许就藏在里面?最好您亲自去看一下。”
特里福诺夫注意地听着,并观察着首长的每个举动。他感到中校说话和举动都显得十分心不在焉,也许他头脑里正忙着考虑别的事情。
他没有猜错。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想的正是主要问题,他的全部计划得靠它来实现。
“听着,特里福诺夫同志,”他友好地对助手说,“您认不认识年龄15岁左右的女孩子?要聪敏、勇敢、机灵,最好有音乐才能。”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的所有助手都知道首长的计划,并不止一次思考、商量和评论这些计划:因此,特里福诺夫一下明白了首长的意图。
“代替阿利姬吗?”他问。
“是。”
“有一个……外甥女,但是她不合适,中校同志,“他想了想作了回答,但随即又说明,”她是个慌张鬼。有点什么事,立刻就尖叫起来。阿利娅,像您所说的教授的女儿……书读得很多,懂得很多东西。这样的女孩没有……
不适合!女邻居倒有个女儿,不过话太多,是个饶舌的人!她什么都会讲出来的。”
“是……这样的人不适合,”伊万·瓦西里那维奇同意,“当然,可以说女孩子撤退到了姑母的村子里,但问题不在这儿,多一个人在住宅里对我们有好处。阿列克谢耶夫每天要学习。”
“要是阿利娅自己同意,为什么不呢?”
“不,我也想到过这点。太冒险。他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很亲密的,哥哥和妹妹。那个女孩见到阿列克谢耶夫会害羞,并且一般说来他们是很不同的……”
“那么,或许他自己有个认识的女孩子?”特里福诺夫问。
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抬起头,仔细地看了看助手,笑了。
“这点我倒没有想到……这真是个好想法。应该问明白……在马尔采夫来之前我们还有许多时间。”
这时外面响起了警报声。伊万·瓦西里那维奇打开了扩音器,听这个令人不安的声音响了几分钟,随后拔掉了插头。
“天气转晴了,他们又飞了,”他说。
“这是某种校正射击用的飞机。在我们战线上没有轰炸机出现,”特里福诺夫说。
“谁晓得他们。今天没有,昨天可能有……”43年,空袭警报在列宁格勒很少出现。空中优势完全转到苏军这边来了,希特勒分子只在战线最紧要的地方派出他们的飞机。